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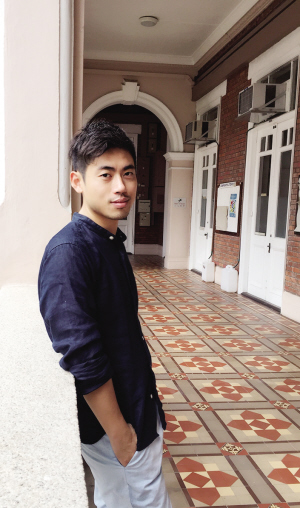
葛亮,1978年出生,原籍南京,现居香港。哲学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著有长篇小说《朱雀》《北鸢》,小说集《七声》《谜鸦》《浣熊》《戏年》《相忘江湖的鱼》,散文集《小山河》等。

印 象
用小说的方式
完成天津怀旧之旅
葛亮是当下华语文学界最受瞩目的新生代作家之一。
今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葛亮的新作《北鸢》。关于此书的创作缘起,葛亮谈到,出版祖父葛康俞遗作《据几曾看》的编辑给他写信,希望他从家人的角度写一写祖父的过往。葛亮接受建议,开始构思这部小说。
《北鸢》整个故事着墨于民国时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半生命运的沉浮。卢文笙的原型是葛亮的外公。为何祖父“成了”外公?葛亮说:“我的祖父一生中与时代、政治保持距离,寄情于单纯的历史、艺术。我的外公却是一个有趣的人,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目睹了某一阶层从繁华到衰败的全过程,但始终冷静、温和、正直地活着。”
在书中,真实与虚构的人物交替出现,比如通过讲述以军阀褚玉璞为原型的石玉璞(卢文笙的姨夫)的故事,引出张学良、张宗昌等历史人物。其中很多情节发生在天津,提到了劝业场、谦祥益、煎饼馃子等与天津有关的细节。出于这一原因,记者通过微信联系上了身在香港的葛亮。
少年时,父亲常带葛亮听昆曲、淘古书,指导他阅读古代笔记,给他讲祖父的故事。葛亮也养成了迷恋旧物的习惯,从恋物中摸索出的源于古典的情感,让他拥有了独特的宁静。采访时,即使未曾谋面,也能时时感受到他的礼貌和教养。
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葛亮到香港大学读研究生,读书、工作,安稳地过了十几年。让他脱颖而出的,除了俊朗的外形,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古典气韵,更有其一贯严谨的写作态度。《朱雀》写了五年,《北鸢》写了七年。速成的时代,能花费七年时间打磨一部小说,实属难得。他把大量精力用在考据上,单是写天津寓公,他就曾几次实地考察天津的旧租界。
葛亮并不希望别人把他当成生活在现代的古人。他也喜欢唱歌、打网球,从没想过要从现代生活中抽身而出。就像《北鸢》出版后他再回天津,用直播的方式做了一次“怀旧之旅”,这是当下最时髦的方式。他去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拜访冯老师。“很震撼,收获也很大,冯骥才老师这些年对于传统建筑的保护做了卓著贡献。他的很多观念,令我佩服并感同身受。天津的民间有许多的好东西,保留与挖掘都是很有必要的。”随后,在文史专家王振良的陪同下,循着外公幼时的成长轨迹,葛亮探寻了天津的一些历史遗迹。比如外公曾就读的耀华中学、过去的意大利租界、督办衙门的原址。“虽然有的地方物是人非,甚至物亦非,但这一程下来,感觉《北鸢》这部小说与我个人之间的联络,更为饱满和丰盈了。”他写下一首诗:“此情可待成追忆,时间如海自钩沉。曾在天津看落晖,民国有鸢落北天。”
天津是我外公人生的起点
与我有血缘上的亲近感
记者:您最初想要写《北鸢》是源于家族故事,为什么会把前几章的焦点放在天津?天津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葛亮:天津是我外公幼时生活的地方,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人生的起点。上世纪20年代,外公随母亲与姨父母生活。姨父褚玉璞(书中名为石玉璞)当时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民国新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在《秋海棠》中曾写过他,是有些脸谱化的写法。在这个小说中,我刻画他,让他回归了家庭本位。我外公小时就住在天津督办衙门里,就是以前的海防公所,后来给日本人炸掉了,现在是天津河北区金钢公园所在地。后来因为北伐,军阀阶层凋落,全家人都搬到了意大利租界。可以说,我外公幼时亲眼目睹了家庭的兴衰,对他性情的塑成有着决定性作用。他人很温和,心地也开阔,愿意和时代达成和解。这一点也间接地影响了我。
记者:写作《北鸢》的过程,应该也是您对天津逐步了解的过程,请您谈谈您对天津历史和当下的认知?
葛亮:天津在民国时期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曾是北京的政治后院,但不仅于此。在研究和书写寓公的过程中,我逐渐触摸到了一个文化品质鲜明的天津。寓公来源复杂,有徐世昌、黎元洪这样下野的北洋政府权臣,也有前清王室贵胄,甚而十月革命后无所归依的沙俄公使。天津曾有九国租界,文化的多元品性,几经碰撞和融合,使得这座城市在历史上曾经是相当有活力的。它很时髦,是中国北方的时尚标的。所以我写到襄城这座北方小城,在不同的层面,都以天津为文化模板。天津的娱乐业也曾经相当发达,劝业场的“八大天”,可与沪风相类,当时有“北有劝业场,南有大世界”之称。有这样的历史基因,我想这座城市必然很可书写。重点是寻找相应的维度。
记者:您的小说中提到很多天津的细节,比如说意租界、劝业场、谦祥益、蓟州独乐寺,甚至煎饼馃子,您是如何发现这些细节的?
葛亮:不少是我外公和祖辈们讲述的经历。也有是从资料的查考中得来,当然田野考察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之前来天津数次,都是为了作相应的实地考察,直观的感受和认识,与抽象的格物还是不太一样。前者更有温度,好像亲自触摸到了历史的脉搏,是血缘和地缘上双重的亲近感。所以,小说有不少细节都是很日常的。天津对我而言,又和故乡南京有叠合的一面。历史沉淀丰厚,城市格局又相当的日常,是过日子的城市。这一点特别符合小说的气性。
记者:您生于南京,一直生活在香港,您的小说写过南京和香港,莫言评价您的小说有人文地理的概念。在小说中将城市做具象化的表现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为什么地域在您的小说中会显得特别重要?
葛亮:我就以新小说《北鸢》为例谈谈吧。是的,我很重视“空间”的意义,尤其是城市空间。但它们对我而言不是生硬与概念化的。我通过它们与历史的交缠赋予其个性。这种个性犹如生命的机体,有它的萌生、辉煌乃至凋落的过程,而时间的印痕则由此千秋各异。尤其在《北鸢》中出现的三座城市,当在同一个世代并存的时候,随着主人公文笙的游走,形成了不同时空多层次的对话。一来它们各自象征了文笙的某一人生阶段,实现了时间层面的融通与比对,同时它们彼此之间又构成更为微妙的互文。比方襄城的照相馆里,有“平津八景”的布景。代表着前者对后者的心向往之,这是一种十分有意味的空间叠合的关系,也代表着文化层面的强弱比对。于我自身而言,这种感觉也来自迁徙的经验,当我初来香港的时候,发现香港还留存着“先施”和“永安”,而上海的四大公司已经了无痕迹,颇有穿越之感。这种空间的流动所带来的时间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最喜欢的现代作家是沈从文
好作品应经得起传统语境的检验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您觉得自己这些年在写作风格上有哪些变化,您如何定义自己作品中的美学?
葛亮:我开始写作实出偶然,当时在读研究生。出于对研究对象的尊重,觉得要真正到位地体会文本应该将心比心。所以自己开始写小说。后来得了一些奖,获得了出版机会,写作也就变得规律。早期像《谜鸦》这样的作品还是比较有实验性的。如果说我的写作风格有较大的变化,体现在我开始写长篇小说系列“中国三部曲”的过程中。这几部作品有相应的时空跨度,人物众多,在布局上需要用心。这种谋篇的意识,在写《朱雀》时已然存在。当时有许多想法,希望通过这部小说来容纳与实现。一方面,源于逻辑感的帮助,对篇幅的驾驭与掌控是我致力较多的部分。包括中国古典式“穿插藏闪”技巧,抑或“后设”叙事的运用,也都尝试融入整体的文本格局中。其中也会设置一些阅读的机关,留待读者与我共同完成。另一方面,《朱雀》起笔时,因为年轻,还是较为专注自我表达的逻辑,包括与读者的文本互动,也更多建立在此前提之上。《北鸢》的文字体量更大一些,写作技法对《朱雀》有所承接。而因为这一阶段我的文学观与人生观,已与前不同,再加之多年资料的积累、沉淀与消化,在开笔已明确这部小说的逻辑是时代运转变迁本身,牵涉一种宏大的历史因果。因此整体结构,顺其自然,不力求形式上自我意识的累加。相对而言,是一部更为沉着安静的小说。
记者:能否谈谈您在写作上的师承,您的叙事风格有一种中国古典式的唯美,我能想到的是苏童、格非、严歌苓、张爱玲的一些小说。您受哪些作家的影响比较大?您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哪些?
葛亮:我最喜欢的现代作家是沈从文先生。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语言审美上的接近。同时他有一个观念,对我的小说创作启发很大。他在长篇小说《长河》中,提出有关“常”与“变”的问题。他认为现代性的东西好不好,是要放在传统的语境中去检验的。这个命题,沈从文先生并没有解决。但命题本身价值很大。这也正是我在小说《朱雀》乃至《北鸢》中想去处理的。传统在当下的意义是什么?所谓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它的链接节点在哪里?这一点特别体现在语言上,中国的语言体系受到两次大的断裂。“五四”那次显然是与现代性的选择相关。所谓时代审美,在开拓可能性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拘囿。这是我想探讨的内容。
还有一位德国作家,对我少年时期的影响很大。帕特里克·聚斯金德,他文字中有种圆熟的纯净感,十分难得。
记者:写作、文学在您的生命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您觉得从事文学是您的幸运吗?
葛亮:写作是我内心的沉淀之道。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被城市的节奏所影响。写作是我不断确立自我的过程。
好故事是建构文本的前提
想写与以往气质不同的小说
记者:其实从大众读者角度来看,您的小说并不属于通俗文学,您在写作的时候考虑读者的感受吗?您如何理解小说中故事的重要性?
葛亮:我重视我的读者,同时也遵从自己的内心。我对我的读者很放心。这么多年,他们和我共同成长,彼此等待。这已经达成一种默契了。“故事”是我小说观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小说传统中的核心内容。讲好一个故事,是我树立小说审美标准乃至建构文本的前提。
记者:您会去写一些类型小说吗?会写市场化的、或为拍电影而写的小说吗?
葛亮:我最近写了一系列悬疑风的小说,这是我尝试写作可能性的一个面向。写作是独立的行为。我的作品被改编为影视,我乐见其成。但我的写作还是会以小说本身为原点,不太会直接受到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
记者:您自幼因为家族原因受古典文化熏陶,迷恋旧事物,但您又是很时尚的青年,两者间如何找到平衡?年轻人会用什么眼光去看历史?
葛亮: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写完《朱雀》时,我尚不满30岁,因此涉及到一个历史书写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既然不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怎么表达是颇费思量的。和上一辈的作家相较,他们可能更多是历史的亲历者,依赖于个人经验,当下年轻作者触碰历史更多是依赖想象。但当我完成《北鸢》时,无论是对历史的认知,包括自己的写作立场,都发生了变化。对于当时处理所谓的“想象”和“再现”的问题,已不是我现阶段考量的重心。在写《北鸢》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要求将自己置于“在场者”的地位。这也是我为何会为这部小说大量进行格物工作的因由。缺乏有关那个时代的细节,所有的想象都是无本之木。换言之,如果你对历史没有一种在场感的把握的话,那么怎样带你的读者进入你想要勾勒和建构的历史情境呢。
记者:您现在最想做什么?接下来“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会写什么内容?
葛亮:最近想做的事情,或许是写一组与以往文字的风格气质不同的小说,比如像刚才说的悬疑风的作品。我有个很喜欢的日本推理小说家,叫横沟正史。推理小说对人性考验的维度,在纵深上有特别的意义。“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则仍关乎中国近现代史,会以晚清为起点。但会将题材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中,考察中西文化的互涉,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会造就何种文化变体的可能性。
葛亮小说《北鸢》中的
天津元素
● 栗子 │ 民国十六年秋,笙哥儿随母亲住进了直隶军务督办衙门的官邸……京津秋寒来得早,十月未过,房里已生起了炉火。昭德在床上躺起身,觉得好了些,就叫底下人取了些栗子在火上烤。姊妹两个,蘸着蜜糖吃。栗子噼啪作响,没有人说话,倒也不觉得冷清……
● 戏院 │ 这“汉升”坐落在南门外河西街吴家桥西堍,还是老戏院的作派。到底已开了四十多年,只是那挂在廊檐下的牌匾,上面就积了铜钱厚的尘土。字究竟也有些斑驳,是让年月给蚀的。这一番上下,比起近在咫尺的“俪和”,就显出了些破落相来。可穿过门厅,走了进去,才知道这所谓破落,其实是一份气定神闲……远远的,一个士绅模样的老者一挥手,便有一个热毛巾把旋转着飞过来。老者手伸在半空,一把擒住。抛得利落,接得也漂亮。堂倌穿梭在人群里,是忙而不乱。
● 劝业场 │ 昭如听说年初法租界刚刚开了劝业场,竟还没去过。便抱了笙哥儿,叫上二姨太一道,说去看一看。这一看,还真见了世面,心想,到底是西洋人的手笔,倒似到了一个花花世界。五层的大楼,外头建得像个洋人的宫殿一般,里面却是个大市集。眼花缭乱间,她便也买了许多东西,欢天喜地地回来。
● 谦祥益 │ 这亲戚叫孟养辉,章丘旧军孟氏。其叔父便是大名鼎鼎的孟雒川,从亚圣第六十九代。要论起族中排序,便与昭德昭如同辈。但这旧军孟氏,上承圣贤,却实在是其中的一个异数。打从孟传熙开始,无意文章,毅然投身商贾。到了这孟雒川,渐渐做出了名堂。主营绸布与茶叶生意,商号渐遍布鲁豫、冀东、苏浙,仅以进修堂创办的“祥”字为号,便有瑞蚨祥、益和祥、庆祥、瑞生祥数十家之众。声名渐居当世陶朱之首,民间便有一说:“山西康百万,山东袁子兰,两个财神爷,抵不上孟雒川。”这天津的产业,由孟养辉经营,号“谦祥益”,有保记、辰记两家大绸缎庄。
● 煎饼馃子 │ 石玉璞是在一个清晨离开的。那是一个很平常的早晨。饭桌上,这男人并没有多说些什么,他只是抱怨了煎饼馃子的味道大不如前。昭德说,天津卫居然还能找得到地道的煎饼馃子,已经是造化了。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