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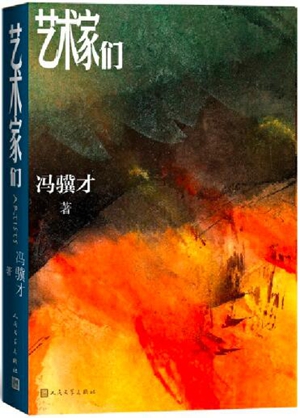
《小说史学面面观》,陈平原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摆在面前的《小说史学面面观》颇类陈平原教授以往的著作封面设计风格,米色纸面中央是一幅汉画像砖的花纹剖面图——这也是鲁迅所钟爱的艺术。下为繁体手迹“小说史学面面观”一行大字,朴素简洁中自有一种厚重感。但有所不同的是,这是新冠疫情中的一次特殊写作,也是作者述学文体的一次大胆尝试。书中小引提到,这并非严格的专业论文,更接近于学术随笔;后记也说,各章原载于《文艺争鸣》的“随笔体”专栏,想试验的是“既学问,也人情,还文章”的一种文体,作者自问“这可能吗”,但可能性只有在尝试过后才见分晓,眼前的著作便是试验田中生长出的第一丛秀穗。待读者合卷时,或许会回想并恍然于作者的这番设想,因为这本疫情之下的特殊之作实则兼具学术史、学术随笔、课堂讲稿的三重性质,且三者并不是分块孤立,而是相互呼应浑融,乃至共同形构出一种学术文体。
01
关于小说史的学术史
陈平原早年治小说史享誉学界,《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等作品几可谓脍炙人口,《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等也具有相当的学术口碑。90年代中期以后,他转向学术史、教育史以及图像研究等领域,成果依旧不凡,但他却觉得,“学界很多人对我的印象,还是早年的小说史研究”,可见开头“亮相”之关键。不过,从最初的小说史研究,到后来探讨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著述方式的学术史(包括小说史),我们仿佛能看到内在思路的勾连和切换。
如果说1993—1994年相继写成的《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和《假设与求证——胡适的文学史研究》是转换中的牛刀小试,2004年的《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则鲜明透露出对“小说史学”进行学术史组建的系统性考量。将新著的《小说史学面面观》置于这一序列显得水到而渠成,书中所选范例融汇史学、批评、理论等多种视野,如同一个多棱镜,折射出小说史学多样性。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部关于小说史的别样学术史。
《小说史学面面观》的史学面目,首先当然在于依照学人活动时代,评述自鲁迅、胡适、阿英、普实克((JaroslavPrusek)、夏志清、韩南(Patrick Hanan)、范伯群、严家炎、赵园、黄子平、王德威以至作者本人三代十二位风格各异的中外学者,呈现各家学术面貌,并揭橥代际流动间学术范式的转移。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作者以史家眼光考稽诸作的“上下左右”——前后相关著作的承变,各版本之间标题、篇章布局乃至内容等方面的调整。这些变化与调适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也关乎小说史学厕身的时代语境和文化空间,在此基础上,历史的时空被撑开,我们才能理解孕育和制约一代学人的可能是什么。
书写小说史学的学术史,作品之外,陈平原也颇花笔墨来谈会议、丛书、出版、项目、评奖等学术组织工作。这有两重意义,第一是勾勒小说史学所维系的体制、机制因素,使得纸上的学问立体活动起来;第二,这与陈平原对人文学的整体理解有关:“人文学更多依赖个体智慧,没必要都搞成大兵团作战。可另外一方面,学界确实需要少数德高望重且公正无私的学术组织者。因此,谈论学人之得失,著作之外,还得兼及其组织能力与引领作用。”小说史学也是学人活动的舞台,台上唱戏的角色固然重要,但没有搭台奏乐,好戏也难以开演。可见在陈平原的脑海中,有一个名为“学界”的共同体概念存在,彼此之间有分工、有协作,才能将学术格局推至宏大精微。
除鲁迅、胡适、阿英、普实克外,书中学人大都是作者有所交游的师友。作为“史”,似乎本应有更长时段的间距方能远观评剖,这点作者在书中亦有提及:“文学批评,最好是同代;史学研究,则更倾向于隔代——至少要有隔代的感觉,否则评价容易偏差。”但因各位学人代表作均已问世有年,故能于沉浸醲郁之后细数其中点滴,且作为同时代的在场者,陈平原其实另有一番特殊优势:对学人心境的体察更为熨帖。
陈平原无疑是一位兴趣广泛而又细心敏锐的人文观察者,早年出版《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纵谈世纪之交的种种文化现象,从学术史、武侠小说,到文化人与学院派的分工、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等等无所不谈,且均有独到见解。他自谦自己只是“业余爱好者”,但通熟文史的他亦明白,历史的叙述离不开时人的观察,“焉知今日粗浅的描绘与论述,他年不会成为学者有用的史料?”《小说史学面面观》中保留的座谈会记录、写给学校的报告、时人言论,也不乏存史以资来者参考的意义;而“注重历史溯源,强调当代人的切身感受”的方法一以贯之,因此才有书中,对那些隐匿在文本背后的位置感和学术心情的微妙感受力。但熨帖、感同身受并不意味着“商业互吹”,实际上,陈平原几乎道出了各家长短,这是史家的“史识”所在。
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平原之“观”小说史,是以自身治小说的丰富经历和博览群书形成的鉴赏力为底子的。他欣赏以范伯群为首的苏州大学通俗文学研究团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学术战略眼光和执行力,以及在学术冲刺阶段,为争取通俗小说的合法性而倾尽全力的态度,也警惕把通俗文学的文化内涵推向极致的倾向。但谈及以“雅俗对峙”作为“小说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力”这一理想思路,陈平原并不像一般的批评家一样坐而论道,而是慨叹“批评容易,建设很难”,因为当年自己做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时便意识到,要将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放在一起论述,“无论如何绞尽脑汁,都是吃力不讨好”。正因个中曲折都经历过,诸般方法的可能性与限度都心中有数,方能“将心比心”,发而为持平中肯之论。
文学研究重视艺术感觉,但学术史研究除了良好的艺术品位之外,也需要“操千曲而后晓声”的学术实践,因此小说史学的学术史建构,离不开学者的厚殖累积。书中第一章提到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之所以能深入,得益于其丰富的小说创作经验,陈平原关于小说史的学术史研究之能洞幽烛微,也或是多年钻研小说史练就一双慧眼之故。
另一方面,陈平原也在审视小说史学的八方来路中反顾自家,使得这部学术史也处处渗透着“我”的个人精神向度。《社会概观与小说艺术——关于〈晚清小说史〉及其他》的最后一节是“与阿英先生结缘”,提到自己早年对阿英整理小说史料的纰漏过于严苛,后来自己亲自动手编辑资料选,才体会到前人的不易。这则曾在不同场合被作者讲述的故事里,蕴藏了一份对于素未谋面而又受益颇深的前辈的歉意和致谢。这显然不是一个总括全文式的收尾,甚至谈不上“余论”,但当这些个人思想史上的成熟蜕变时刻形诸纸面时,我们隐约能辨别出一种温柔敦厚的诗学意味。陈平原也提到自己在80年代后期过分强调普实克个别偏颇的论述,而忽视他的晚清小说研究的提倡之功,现在重读旧作,也感到并不妥——其实也不必介怀,不少北大中文系的学子,正是在陈平原的课堂和文字间,邂逅阿英及普实克等前辈学人,并知道了他们的伟大。
对于一位以治小说史出身的学者而言,写作一部关于小说史学的学术史,不可避免地会与自身的思想轨迹发生诸多交错,因此这部学术史也可以是自家的精神成长小史,这便涉及了《小说史学面面观》作为学术史之“别样”的问题。
02
学术如何随笔
就“学术随笔”的脉络来说,90年代有“学者散文热”,但学者散文可以不谈或主要不谈学术,而《小说史学面面观》依然有“研究对象”和“研究旨趣”的意识,引文、脚注的严谨丝毫不让一般的学术专著,即依然是以学术规范谈学术问题;不过文字兼及师友杂忆,不时宕开一笔谈交谊、谈亲历、谈感受、谈学者的人间情怀,各家性情溢出纸面:踌躇满志而又转身寂寞的夏志清,温文尔雅、低调内敛的韩南,严谨求实中又有开拓进取的严家炎……如同现身舞台的聚光灯下,个个光彩照人,这固然是由于各家学术面貌的突出,但作者文笔的聚焦之力绝不容忽视。
陈平原在小引中谈到,讲课须得“大珠小珠落玉盘”,这确是多年授课的经验之谈,亦一语道出学术随笔的关键。《小说史学面面观》读来既不乏真知灼见,却也毫无板起面孔说学术的压迫感,令人想起陈平原在世纪之交提出的一个经典说法——“触摸历史”。在他的笔下,历史是可以触摸的,有温度,有质感,更有跳动的脉搏;在以传述学人立场、方法、趣味为主的学术史中,带入“人”的因素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倘若这些因素直接关涉个人经验,夹杂在“正史”缝隙里的人事和心情便自然地以随笔形式出之。当我们乍从“普夏论战”“抒情与史诗”的学理性分析中回过神来,作者的笔墨已经延伸到身为汉学家的普实克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感动的余波尚存,而作者笔锋一转来到意识形态转型后海外中国学的窘况,历史的抒情与现实的理性并存一纸,张弛之间波澜迭起。更有意思的是,作为大变革时代的见证者,作者本人的阅读和重访东欧的经历也被纳入,以自身的体验共振时代,发出的思考尤为深挚。这类叙写之笔于课堂现场是点睛,于日后回想起则是弥漫在回忆中的“水分和空气”,合书冥想,我们感受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气氛。
读者很容易注意到,每章开头皆有一段导入,而自第三章阿英起,导入渐成有作者本人介入的“学术小插曲”,这可能是自己当年读学人追忆时的心灵震撼,也可能是对某场参与过的学术活动的回顾,甚至可能是一个有些俏皮的同门谈天场面:“告知师姐,这学期我在北大讲授专题课‘中国现代文学文类研究’,讨论的对象包括她早年作品《论小说十家》,她有点儿困惑,以为这纯属‘徇私舞弊’。”然而这倒不是作者在“挟文化资本以自重”,因为我们很快发现,作者的出场并不喧宾夺主,大多数时候他是在提供一个亲切的视角,让读者借助他的眼睛,看见学人在学术论述之外的言谈容止,而这些与他们的学问并不可截然分开。
这种作者的“主观性”视角贯穿了《小说史学面面观》的全书,也正因此与当前一般的学术文体区分开。关于述学文体的主观性问题,在全书的第九章“阅读感受与述学文体”有深刻的展开。第九章中谈论的正是陈平原的同门师姐赵园,书中引用了赵园散文选集《旧日庭院》的一段跋文:“散文不同于论文,有可能更直接地面对个人经验,其实论文何尝与个人经验无关,只不过其间的关系较为隐蔽曲折罢了。……运用何种文体,在我看来,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盛载了什么。散文有可能与‘性灵’无干,甚至示人以卑琐;论文也不妨充溢着生命感,是别一格的‘美文’。”赵园直截了当地表明论文与个人经验的隐秘(在她那儿甚至可能是公开的)关联,这很有可能让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学术的“客观性”的写作者大吃一惊。陈平原则认为最后一句是赵园为自家文体“辩护”的夫子自道,他并不直接示意可否,但从他提出的文学史家的“识大体”和“辨小异”中可以看出,他欣赏那份“拒绝平庸的文体”的气度和自我期许。
其实,“论文”是否可以“美文”,或“学术”是否可以“随笔”,类似的问题本身就指涉出某种关于“论文”或“学术”的普遍想象,如少修饰的、去主观化的等等。这种想象并无所谓对错,但在当前的学术生产中,显然有固化乃至扼杀其他可能的趋势。跳出一步来看,人文学对于“纯粹客观”的追求会不会也只是一种历史的建构?
在这种情况下来读《小说史学面面观》,会发现作者始终在极力呈现的“面”,正是小说史学之文体的多样性。无论是赵园充满主观性的小说评论,还是普实克投注极大生命体验的中国文学研究,抑或是王德威瑰丽细腻、流动婉约而被推为“散文典范”的作家论,乃至作者自身所试验的“随笔体”学术史……越过虚设的学术文藩篱,作者把这些在当前学术格局中显得有些陌生、异质的东西收进小说史学的万花筒,这种选择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
陈平原曾在多处强调述学文体的重要性:“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现代中国学者亟需锤炼的基本功。”“可以有‘偏见’,但不能没有‘自觉’。”2020年《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一书横空出世,追述、领略现代学术体制确立前的文体,才知本无天然成理的定制。
可以说,陈平原是有高度文体自觉意识的,他的学术著作文字清通,睿智风趣中可见洒脱胸怀,具有个性化的辨识度。而《小说史学面面观》在此基础上,试验的是一种更为生活化、情境化的文体。具体说来,《小说史学面面观》虽然采用了“以我观世”的视角,但与赵园的独居书斋的“召唤式独语”不同,作者需要在个人阅读和公开授课间维持平衡,因而他的情绪输出是相当节制的。他用“我注意到”“我猜想”“我则以为”这一类以“我”为主语的句式来分享他的观察,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陈平原在“看”一个时代。多年治学和眼界的积累,使得他的观察介于生活经验和历史规律之间,具有从细节、情境连接到学统、文脉、时代等更为深邃的命题的洞察力。对于读者而言,阅读的既是小说史家的学术思考,也是一个80年代开始“亮相”学术舞台的学者的“人间观察录”。
学界大多对陈平原的学术著作有所了解,但其实他的散文随笔也饶有风致。《阅读日本》《大英博物馆日记》《书里书外》等文集以访学、出游、读书、怀人经历为主,在风景古迹、书卷图画中点染着人文学者的关怀和思考——毕竟是学人本色。笔致散淡,但延伸出的话题却与《小说史学面面观》相映成趣,芜湖访阿英藏书的始末(《江南读书记·芜湖》)、苏州读鸳蝴小说而产生对于通俗文学的判断(《江南读书记·苏州》),都在直接处理个人经验的散文中得以铺展开。这也暗示我们,学术随笔中看似漫不经心的晕染,其实也需要恰到好处的掌控,即使有很多津津乐道的细节,与此篇学术旨趣无关的也不应迷恋。数书对读,便可以观察到陈平原是如何延续随笔的风趣和生活观察的视角,并剪裁个人经验妥帖安置在学术文章中。
在《文艺争鸣》上设立“随笔体”专栏是陈平原的主意,这一看似有些“顽皮”的试验之举,也显现出这位人文学者的可爱之处:不向僵化的定制妥协,倾心于好文章,永远走在探索学术与文章之可能的路上。其实,写随笔不仅是寄意遥深,亦有安顿身心的抒怀意味,只是在日益严苛的学术考评中,这种拨弄文字的快乐已不可多得。或许,站在陈平原的位置上做此事,亦是别有幽怀。如何为青年学人争取更大的空间,帮助他们在现有学术体制中获得一种张弛有度的精神生活,他是关心的。
03
文学课堂与对话青年
听过陈平原授课的人大概都会承认,他的课堂是极富魅力的,令人想起他追溯过的鲁迅的文学史课堂——挥洒自如,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或许正如对学术文体的清晰自觉,他也在授课的艺术上用心经营。《小说史学面面观》的主体内容原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课程的讲稿,读文而课堂风采宛然,亦可见“随笔体”与课堂语境之相辅相成。
课堂以口头表达为主,自有其预期听众和传播效果的考虑。如第一章的“文言述学与学界边缘”、第二章的“述学文体与文章结构”分别论及鲁迅与胡适的述学文体,此前陈平原亦有撰文对这些问题进行处理,但两相比较便可看出,《小说史学面面观》的篇幅凝练,缩减了繁复绵密的论证过程,只提炼关键信息,多用设问、反问和第一人称视角,偶一冒出绝妙的口语化譬喻,除了个性洒露外,也是课堂本色使然。
陈平原1987年博士毕业即留在北大中文系任教,与“在边缘处策马扬鞭”的同辈好友黄子平相反,陈平原始终是中国高等教育中心的“在场者”。既是学者,也是师者,这让陈平原保持与每一代青年人共情和对话的必要感和能力;同时,从80年代以来一路热眼旁观学院内的种种变迁,他对学术范式转移下的利与弊也有权衡。
《小说史学面面观》所择的三代十二家,基本都实现了“经典化”的过程,但陈平原的目的显然不在于“让经典更经典”,而是尝试打开经典内部,发掘出特定时代的学术原生力,这恰恰可能是近乎“学院化”的当代青年学子最为陌生的。书中不止一次对90年代后的学术风气表示担忧:现代文学专业学生的作品阅读量骤减,文本感受力迟钝,学术研究背后缺乏主观投入,学术文体的千人一面等等。的确,与陈平原等80年代学人相比,90年代之后的学生在知识积累和理论训练方面或有所提升,但反过来说,90后相较80后缺少较为深厚的人生经验,在融合生命与学问的境界上,难以望其项背。随着博士培养机制的完善,学术生产的流程完整而高效,但却愈来愈像一种流水线上的工作,让人觉得缺少些灵气与活力。在此背景下,“文学如何教育”也是身为教育者不得不思虑的问题。现代教育依赖课堂,因此文学课堂除了基本的传授知识,也担负着交流思想、传递学术经验,以及促生反思与新变的重任。
不过,用意可深,而行迹宜浅。陈平原的课堂极少说教式的高谈阔论,《小说史学面面观》中也不见什么“摇旗呐喊”的姿态,他的启悟和对话意图都是不动声色的。他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先是抛出一个疑窦,夏著和英美新批评究竟有什么关联?都说夏志清受新批评的影响,可明明新批评的方法与长篇小说批评风马牛不相及。接着陈平原循其生平、言论、著作去追踪,最后揭示出一代名家的撒手锏其实不是一般认为的学院派方法,而是长期阅读养成的良好品味,这是最为朴实无华的文学研究路径,却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经过几番淘洗仍能在学界立住脚跟的缘故。
亮出问题,抽丝剥茧,最后图穷匕见,这样的叙述方式逻辑清晰且吸引力十足,极适宜于课堂讲授。剥去理论的外衣,点出立场的偏见,最后定格在“阅读经典”的内核上,持论中正而侧重点一目了然,配合陈平原不疾不徐而又坚定清晰的语调,无论你认不认可,这个深刻的印象是留下了。
与夏志清的“一空依傍”式阅读相似的是赵园,谈论赵园一节中选录的学生反馈,则展示了陈平原课堂上师生互动的一角。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类研究”课程中,陈平原特意留出一部分时间与学生交流。不难看出,学生对赵园文体特点的把握都是到位的,只是在主观态度上有别,陈平原也并不判定言论的高下,他更关心的,是学生是否从中感受到学术研究的热情与生命力,是否依然相信“直面文本”的力量,这较之简单的“好”与“坏”,似乎更为关键。
不久后,赵园在《文艺争鸣》中作出回应,虽是因陈平原的文章而发,但亦不无对话现代文学后来学人的用意:
我期待于现代文学后来的学人的,是走出自己的路,包括扩展专业的知识基础:即使不能“兼通”也略知中/外,尤其古/今。
……
其实,“背后”的东西很平常,上面都已经涉及:你的阅读经验、经历,包括你从事学术前的阅读经验、经历;你的自我认知、评估——对于你的可能性,潜能;学术过程中的不断检视,反省,调整。此外,你的人生经历,你的关怀,永远是你从事学术的背景。
赵园的发言真挚深沉,从自身的经验和学术路径出发寄语青年,虽是笔谈,但看到一番与自己有关的回应,青年人所感受到的鼓舞力量不言而喻。在此意义上,《小说史学面面观》的文字与文学课堂一并撬开了学术代际壁垒的一个决口,不同代际学人的学术关怀得以流动、传承,而陈平原的课堂反馈也让我们看到,无论学术范式如何变迁,始终有人在相信,要把学问和自己的最深的生命关切结合起来。
书中最后一章,陈平原梳理了自家十数年的小说研究,因为谈自己,语气仿佛更为严肃,不是借以自威,而是不自矜;也正因谈自己,著作背后的心路历程、回顾中的得与失甚至不需伸手,便可“触摸”。直至今日,陈平原的小说研究仍然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不可绕开的里程碑,独到的选题眼光背后有一代人的机遇,但操作和实现中也有难以复制的独特生命体验。不过,作为面向青年的课堂,陈平原的曲终奏雅选择了一个永恒的话题——梦想,因为不愿重复劳动,追求新境界,他的小说研究样态多端,同样循此思路,他在90年代中期以后走出小说研究,转向其他领域开疆拓土。隔着数十年的光阴望去,80年代的学术依旧给人朝气蓬勃之感,很难言明那种精彩是什么,但陈平原的话似乎让我们窥见了一点:年少气盛与新见迭出,那是个人生命史与学术史共同大放异彩的辉映。一堂课程终有落幕,但人类智慧的星空中,却永远会有青年的梦想闪耀着。
几年前,王家卫用《一代宗师》把逝去已久的“武林”带回大众眼中,谈及构思眼光,他说:“武学千年,胜负都是过眼云烟。我们不在意一招一式,我们在意的是整个武林。”这构成了对于历史演绎的一个隐喻。陈平原的《小说史学面面观》同样展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小说史舞台,虽然他总说自己90年代中期后不再从事小说史研究,但他的目光从不曾真正离开这片舞台。这一次,他转动小说史学的多棱镜,既呈现了诸位大家的五花八门的“招式”,也筑起格局、放眼观察,最终寓意还在深远:“若能呼唤更多新人登台表演,则于愿足矣。”酝酿一种风气,培植学术新人,这也是文学教育以及所有学问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