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艺术家们》着意深描艺术家们的“心居”,隐喻艺术家的灵魂样貌与变迁,在对世俗与俗世成分的剥离中放大“精神至上”“艺术至上”的内核,用叙事的灯塔照亮被庸俗化了的艺术家们的心灵和他们驻足的世界,在时代的青铜雕像上镌刻下一个老艺术家的声音。一部《艺术家们》,其生成的启示意义与价值已超越了冯骥才蕴蓄多年的思考和叙事表达本身,不仅指向“谁是艺术家”蕴含的多维命题,也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突出重围、实现自我精神守望的历史镜像,同时也启迪我们对其忧思的进一步考量和思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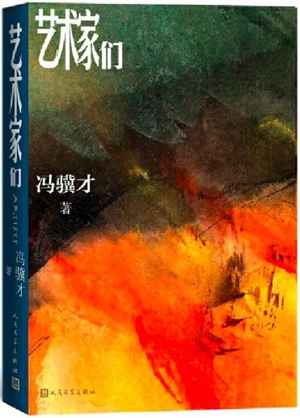
《艺术家们》,冯骥才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
2020年,年近八旬的老艺术家、作家冯骥才,在为抢救文化遗产、“抛书掷笔”近二十年之后,重返文学,奉献出了他的新作《艺术家们》《俗世奇人全本》。虽然,无论是评论界还是作家冯骥才本人,都把它们界定为完全不同的立场、文化与气质的两套笔墨的写作,但我认为,这是两部在精神上暗合、并形成互文的对照文本。前者以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家为书写对象,展现他们半个世纪的艺术情感、伦理、道路的变迁与分化;后者则构筑了一个民间的、俗世意义上的艺术家的世界,在极短小的篇幅内,速笔勾勒出民间手艺人的绝技与精魂。《鼓一张》《崔家炮》《刷子李》《神医王十二》《认牙》《大裤裆》《大关丁》等篇,冯骥才为做年画的、造鞭炮的、看病的、卖艺的、工匠等“民间艺术家”画像时,不仅投映出地域的文化、城市的性格,同时也赋予了他们以艺术家的精神气质:追求技艺的极致、不断的创新与恪守的底线。我想,这也同样是《艺术家们》的底色与基调。一个沉寂了二十年的老艺术家所坚守的艺术理念、追求及思考、困惑在他所构筑的艺术家天地中形象地传达出来,在看似无意间打破了时空界限,在“圣殿”与“俗世”的艺术家谱系之间搭建起灵魂之桥。
其实,冯骥才作为一个小说家、一个画家,对艺术家们的书写愿望源起于上世纪70年代。小说《艺术家的生活圆舞曲》本已定题,但却因种种原因而搁置。这一精神“受孕”持续了整整四十年。在此期间,冯骥才并没有停止对绘画、对不同时代画家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尤其是市场经济大潮下画家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及艺术观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让他愈发怀念虽处在贫瘠文化环境、却对精神充满渴望的1970年代“草根”画家,并将其视为勘察现实的珍贵精神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们》的问世是有迹可循的。
2008年,冯骥才发表短篇小说《顶楼上的歌手:一个在极度压抑下浪漫的故事》,可以看作是《艺术家们》的雏形。从副标题“一个极度压抑下浪漫的故事”,即可判断它与《艺术家们》的“亲缘”关系。《顶楼上的歌手》与小说“前卷”调性极其相似,或者可以说“前卷”是对这个短篇的扩写与改写。文化真空的年代,小阁楼、破败不堪的环境、画家叙事者,对面屋顶阁楼新搬来的邻居的歌声“神奇般地闪闪烁烁”;叙事者反复书写“神灵般的歌声”对“我”心田的滋润,疲惫的消除,绘画灵感的触发,甚至是与“我”心灵的奇妙“对话”和共鸣。“我”也能从歌声中听出他情绪的起伏变化;“他”的歌声被粗暴打断、有断有续;“我”与画家朋友的艺术交流、我们对绘画的坚守;大地震,顶楼的损毁与重建;“我”妻子的温情……故事从时间到空间、从人物到情节、从艺术的痴心、力量到整体氛围,都是《艺术家们》“前卷”叙事的核心元素。“这才是艺术的神奇与伟大。不管物质怎样贫乏、内心怎样压抑,它都能创造出无比丰富的精神和高贵的美来”像回声穿越历史的时空,激越而嘹亮。“中卷”与“后卷”虽将深层思考扩展到艺术家在历史变迁中如何面对时代召唤、如何面对市场挑战、如何自我突破等复杂命题,但于前卷铺陈的理想主义色彩仍弥漫于全篇。精神至上、艺术至上、以美照亮灵魂的艺术伦理、灵魂伦理始终作为精神隐线贯穿,并照亮老艺术家的赤子初心。无论如唐吉诃德般地长期致力于文化遗产抢救事业,还是对艺术家精神气度的理想塑形,冯骥才都身体力行地以“艺术圣徒”的姿态呼唤、捍卫着艺术的精魂与人民艺术家的尊严。
那么,冯骥才的呼唤在当下的意义何在?谁是艺术家?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有着怎样的生存状态?他们应该张扬、恪守怎样的艺术理念?在当代文化空间中应该拥有怎样的生存姿态与精神气质?冯骥才又对艺术家有着怎样的理想化憧憬?冯骥才的“艺术家”们究竟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这些成为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深刻命题。
二
毋庸置疑,“美”与“纯净”“艺术至上”是《艺术家们》审美和叙事的关键词。我在阅读时,常常为这位八旬老人能够拥有如此美的理想与激情而感慨甚至是感动不已。三卷的卷首语“荒原上的野花是美丽的天意”“闪电从乌云钻出来。我的歌啊,你也从囚禁于我的心里飞出来吧”“被美照亮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富翁”,猶如作家的心灵咏叹调,回荡全篇。无疑,对美的追求,是冯骥才赋予“艺术家们”精神气质的要素。那么,如何将这种“美”呈现、诠释,将其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我感到,除直抒胸臆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路径就是空间表征。冯骥才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绘画跟文学共通性的一点是,都要产生视觉的形象,要唤起读者一种形象的想象,要给读者营造一个看得见的空间,看得见的人物,看得见的景象……”显然,作为往返于文字与丹青之间的艺术家,冯骥才对于“看得见的空间”有着更加特别的敏感、迷恋和书写的自觉。他在《艺术家们》中,将艺术家对美的追求做了空间化处理,尤其着意深描家宅空间,“把家宅当作人类灵魂的分析工具”,从直接表征、反差表征和变迁表征三个维度,对应性隐喻艺术家的灵魂样貌与变迁,为艺术家们构筑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心居”。
云天和隋意的尖顶阁楼显然是冯骥才的最爱。他把对这两个人物的偏爱毫无掩饰、毫不吝啬地给予自己能够想象出的所有美好:不俗的家世、姣好的外貌、超凡的才气、脱俗的追求、善良的心性,而这诸多的美好几乎都通过尖顶阁楼获得诗意呈现。一方面,作家不吝笔墨,直接勾勒描画出空间的独特格局及独特韵味:六根柱子将不大空间切碎,“看上去好像在密林深处”;阳光赋予小屋“天生就是活的”的无限魅力;天窗上随季节变换落下的雨水、落叶、落花,大雪封窗后“一点点化开,露出这世界最纯净、最高远和最无穷的蓝色”;屋子里散发着木头的气味,大自然才有的气味……作家没有止于对诗意空间的抒情构筑,而是将主人对房子的深深喜爱融入其中。挂在墙上的云天的画作,隋意用碎布缝成的优美又优雅的靠垫或枕套,让人与空间融为一体,成为诗意空间的一部分,共同组成一幅画、一首诗、一曲歌,建构起“天堂的一角”。另一方面,作家设置他者的眼光来打量、感受、评价这个小屋,在洛夫那里是“古城堡”,在雨菲的眼中则是“太美太神奇”的“像童话里的小屋”。自然、浪漫、远离世俗的艺术之美,足以抵抗物理空间本身的逼仄和压抑,夏天如蒸笼、冬天如冰洞带给人身体感受的不适,而不断去放大心灵感受。同样“化腐朽为神奇”的还有罗潜的小屋。“低矮又简陋”“屋顶和门都有点儿歪,墙皮剥落得厉害”,但却斑驳而又和谐。屋内自制粗糙家具、旧毯子、垫子、陶罐、空酒瓶子的花瓶,野花、叶子、秋草,柜式唱机,都油画般无言散发着怀旧的艺术气息。冯骥才以“尖顶阁楼”“世外僧房”作为他无比喜爱的艺术家们的诗意栖居地。他让青年们在时代社会荒谬的大空间下,开辟出能够安放灵魂的小空间,而对艺术的渴望、对精神的憧憬、对美的创造让本已破败闲置的空间充盈着神圣的氛围。冯骥才在细腻甚至是反复的书写中不断强调、强化家宅空间给他们生活带来无限意义的“神圣”性,以此表征几个“艺术圣徒”对“精神至上”至美追求的心灵面向。
对延年形象的塑造则通过物理空间与心灵空间的巨大反差,产生强烈的视觉冲突与心灵撞击,形成美学张力。年久失修的楼房、受潮的墙面、坑洼的路面,黑暗、潮湿又阴冷的地下室,但从破烂不堪、七零八落的旧三角琴中流淌出的却是明亮、悦耳、极优美的琴音。“音乐是最神奇的艺术,它可以瞬息之间改变整个空间与环境里的氛围,还有你的心境。”流淌的音乐照亮陋室,也照亮人的心灵;老房子里萦绕伟大的音乐经典,充盈着几个年轻人的热爱艺术的激情,由此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神圣空间”。后来,延年“用两间大房子换这间小小的‘牢房’加上一架谁也不要的钢琴”,因为“琴比房子更重要”“我随时可以进入天堂”。当音乐响起,“云天顿时觉得自己不是身在斗室,而是坐在飘在空中的白云之上,享受这清风、阳光、唯宇宙才有的宁静”。无疑,冯骥才以物理空间的“至陋”与精神空间的“至美”的反差张力,书写出一篇极具美感气息的“陋室铭”,为那个时代的青年艺术家们雕刻出灵魂的塑像。
可以看到,冯骥才的“空间诗学”,以“美”为基调,诗意、浪漫、古朴亦或是艺术至上构成“美”的基本内涵。他不仅从正面以空间之美、之陋隐喻人物精神之美,同样也在反向书写中慨叹空间变迁后美的遗失。罗潜灾后重建的小屋“翻旧为新”,云天却觉得失去了旧日味道;云天、隋意建好的新居“不再有往日的那种深幽、古朴与别有洞天,没有了原先的立柱、坡顶、天窗,一切诗意都被实用主义赶跑了”。从此后,那座尖顶小楼一直珍藏于云天和隋意心底,不断追忆,成为无法复制的诗意栖居之地,同时也成为一段流逝岁月的精神地标。“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一座梦想的家宅,一座属于回忆和幻想的家宅,它消失在一段超出真实的过去的阴影中。”“在出生的家宅里建立起了幻想的价值,这是当家宅不复存在之后仍然留存的最后的价值。”“尖顶阁楼”和“世外僧房”虽不是“出生的家宅”,但另一种意义上,却成为艺术生命、精神生命的诞生地。在这里,他们怀揣着艺术梦想,通往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因而,当这个家宅不复存在之后,居所的回忆在现实中不断被重新体验,不仅仍然留存而且扩容了它在青年艺术家们心中的终极价值,就是说旧日“原风景”早已成为他们此后生命的起点,建立艺术与精神伦理坐标系的轴心。
因此,当艺术家偏离轴心而越出“原风景”轨道时,冯骥才便同样以空间来彰显其艺术伦理乃至精神伦理的蜕变。可以说,他对洛夫之变的书写在最初的空间维度就埋下了伏笔。相对于云天和罗潜的家宅空间或诗意或古朴的细描,作为精神符号的个人空间,在洛夫那里最初几乎是空白。作家将视点聚焦到中后卷,关键词从单元房的富有、繁复精工、追求豪华、暴发户的气息,发展到后来带亲水平台的两层大别墅的“华贵”“繁复”“五彩缤纷”“璀璨夺目”“华丽”“闪光”“不伦不类”,他痛心、失望而又略带鄙薄地用了一连串“俗”系列语词,将洛夫艺术追求的蜕变过程进行了“看得见”的空间细描,将其艺术生命乃至个体生命的终结,以空间寓言及预言的形式铺陈出来。对罗潜而言,则是另一种“变”。位于郊区深处的房子,虽保持了他一贯的“深藏不露”风格,但空间内部却是“往日的痕迹一点儿也找不到了”“墙上没有画”“屋内的家具全都应和着一般家具日常实用的规范”,从古朴自然到简单实用、墙上无画、心中无梦,罗潜从“艺术的圣徒”到归于俗世现实的无奈与苍凉,都在空间场景中自动浮现出来。
我曾感觉到阿来“叙事的空间维度”,“他要以空间来表现积淀内蕴于其中的历史留存与变迁”,冯骥才同样以小空间变迁把握住了人及时代变迁的脉搏。他将“家宅”视为艺术家精神的重要表征,将深描贯穿其整个生命发展历程。我们能感受到作家将理想空间、神圣空间与“俗世空间”“世俗空间”对峙的鲜明立场,可以说,这是冯骥才所遵循的艺术家的空间伦理。他所建构的“神圣空间”虽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细部呈现,但却拥有共同的远离尘嚣、清新脱俗、诗意浪漫、古朴自然的本质属性,这是作家对“艺术家”的空间维度的诗性界定。当俗世亦或世俗更多进入这个纯净的空间,“真正的艺术家”便已不在,于是他让洛夫、罗潜分别以不同的方式退场。我感动于作家对神圣空间构筑的不变初心,但同样由此引发了对艺术家与空间关系的思考。如果说“家宅”代表的是艺术家的私人空间,那么,他们又该如何处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远离尘嚣、沉浸于纯粹艺术世界能够实现生命主体、艺术主体的价值吗?“真正的艺术家”是否要遗世独立?他们该如何在艺术创造的独立性与大众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背景下,离群索居是一种困境下弥足珍贵的自我坚守,那么,在充分开放的大文化环境中,像云天那样继续在一个英式老房子里独享幽静、古朴与舒适,是否就是艺术家空间姿态的应有之义?当然,云天也曾到黄河、到壶口瀑布去感受大自然力量的震撼,但作为一个“人文画”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的画中是否缺少一种对“人”的关怀,一种对存在世界、现实问题的关怀?
必须承认艺术家的知识分子身份及精英群体定位,但是,精英群体“应该”如何处理与大众、底层的关系?“应该”如何在艺术创作中践行这种关系?从空间维度看,艺术家的“心居”如果处于封闭状态,走不出去这个“心造”的象牙塔,将自我隔绝于大众之外,那么,他将不仅仅丧失艺术家俯瞰人间大地的悲悯情怀,艺术创造也只能“独上高楼”,独享自创的繁荣和浩瀚。“底层人民的精神空间是一个上天入地、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世界,它的丰富性、原始性、草根性常常是精英群体的文化想象力所不可抵达的。”是否可以这样说,将头颅高高扬起、望向纯粹艺术天空的艺术家,从他斩断与底层大众的精神血脉的那一天,也就拒斥了丰富性、原始性、草根性,他的艺术生命力也就因失去大地的根基,彻底走向狭窄甚至是枯竭。冯骥才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在作品结尾设置了落地民间的“艺术圣徒”高宇奇,让他将艺术足迹踏至城市各个角落,踏至太行山深处,去表现时代大潮中的农民工,去表现留守乡村的老年农民和儿童。画作工程浩大,需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修正、不断超越,可谓是“为了艺术掏干自己”,甚至为此而殒命太行山。高宇奇将至上的艺术精神落地到对被忽视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关怀之上,从自我的小天堂走向广阔的人间大地,我想,这应该是冯骥才对此前悬空的艺术理想的一种补充亦或是自我修正,对此前贯穿的“真正的艺術家”的界定完成了自我的扭转与升华。
看得出来,关于谁是艺术家的命题,冯骥才始终通过隐含作者或人物之口来传递自己的声音:“在艺术上,一旦被别人征服,就会失去了自己。”“进入最高的绘画境界。这个境界既是绝对的自我,又是一种忘我。”“艺术家工作的本质,是在任何地方都让美成为胜利者。”“重复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就意味着死亡。”“真正的艺术创作,每一次都是一次自我的升华。”“他要坚守的是自己的艺术观不在生活的重锤下变形。”……我们看到,这些坚守自己、坚守美的使命、忘我入境、不断超越自我等等,都是艺术家可贵的品质、伦理、原则。但作为一个艺术家,“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悲悯情怀与博大胸襟的声音却那样微弱,幸而有“艺术圣徒”高宇奇的出现,将这个正能量的“大声音”传递出来。
三
除此之外,冯骥才对“神圣空间”的思考,还存在着一个与此相关的俗世生活的维度。他不仅将艺术家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以“偏于一隅”的方式,表现为“相安无事”式的紧张,同样也剥离了其艺术空间内部的俗世成分,“制造”出艺术家与俗世生活的对立。他净化、过滤了云天们生活空间中的俗世成分,将他们几乎置于艺术的“真空”中。云天们将不喜爱的工作、不公正的待遇、生活的艰苦淡化到几近于无,让艺术的、精神的力量战胜一切,让以艺术为核心甚至为“地基”的友情、爱情的“核能”炸裂俗世的迷障。人物关系的处理,是作家的叙事意图、策略,但也同样是生活伦理呈现。冯骥才将艺术家们置于简单的空间关系中,艺术与精神已成为维系他们情感与交往的重要纽带。把三剑客牢牢拧在一起的,是围艺术之炉而取精神之暖;他们友情的基础是对彼此艺术天赋、才华的认可、欣赏。除此之外,非艺术的因素几乎未进入到他们的交往范围,竟至于“云天与罗潜相交十余年,头一次听说他在什么工厂工作,还有一些工人同事”。就是说,他和洛夫了解的罗潜,只是一个小沙龙空间的罗潜,一个“艺术”的罗潜。基于唯艺术的情感、精神甚至灵魂的认同,不仅发生在友情层面,同样扩展流动在神秘美妙的爱情领地。云天和隋意的爱情有着青梅竹马的水到渠成,更源于相互的“欣赏”——“她欣赏云天,欣赏他天生对艺术的非同寻常的感知,还有他的艺术想象。”“她欣赏他文字里常常冒出的灵气。”“而云天欣赏她的,是她对艺术的悟性。他把艺术奉若神明,她似乎是天生的精神至上。”云天和雨菲的相互吸引也是源于艺术的崇拜和对艺术灵气、艺术美感的欣赏,甚至云天对白夜同样是无法抗拒她那种“罕见的美好又清新的气质留在他的心里”及作品的“很有品味,非常独特”。显然,冯骥才设定的艺术家们情感空间的发生机制中,艺术、唯美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甚至是唯一。情感的“排他性”,在这里显现为对非艺术元素的排斥、剔除。那么,艺术的才华、对艺术的挚爱及由此炼就的艺术美感,是否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并将它们之间的种种区别与冲突一并囊括于其中。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纽带和共同根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或方式体现出来。”脱离了日常生活,每个人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形态是不完整的,对艺术灵魂的抵达并非意味着对一个艺术家整体精神世界的抵达。所以,云天对罗潜的认识中留下太多的空白,以至于这个朋友后来的转变、离开只隐约把握到“为了生活而低头”的抽象信息,而其他大量丰满的细节被遮蔽于转变的表象之下,给读者提供了诸多的想象,但也让罗潜曾经“不要变”的坚守失去了结实依托。这让我们不禁发问,这些基于对艺术才华、艺术之美的欣赏、崇拜的情感与关系,是否能经得住艺术象牙塔之外风雨的考验?冯骥才安排了三剑客的渐行渐远、云天与隋意的情感危机,是否是也意识到了“唯艺术”的友情与爱情,禁不住时代与诱惑的洗淘?
我感觉,冯骥才以艺术追求是否纯粹、对艺术精神是否坚守为标准,对艺术家进行衡量与划分:纯粹的、非纯粹的和从纯粹走向非纯粹的。他将叙事的光圈投射到作为艺术家的身体和灵魂侧影中,艺术之外的生活的、或活生生的“人”的全貌被推至、隐藏幕后。其他人在艺术的舞台上登场、亮相,唯有云天是唯一的主角。但我们也只能看到一个理想主义者艺术的良心和他面对艺术家庸俗化时内心的苦痛、自我博弈与渐渐的淡出,就连他的两次情感纠葛都没能离开艺术的“感觉”;隋意的生活也是紧紧围绕艺术,她对艺术的直觉判断、她对生活的艺术化追求、她的温情、她的善解人意,甚至她的两次情感受伤都是带着特有的忧伤与处理方式……艺术真空之中的舞者,在谢幕之后,进入俗世生活中鲜活、生动、真实、可信的那个“素颜”面容,被作者“雪藏”在巨大的空白之中。俗世生活的缺席,让艺术家们的形象“扁平”起来,也“苍白”起来,对“艺术”维度的强调,遮蔽了其作为“人”的多维复杂性。
当然,冯骥才并未完全回避俗世生活对艺术家精神世界的侵入甚至是扭转。他让罗潜说出了“远离市场可以,前提是不缺钱用。为了生存,或生活得好一些,最终还得服从市场”。云天内心也充满自我的问诘与博弈:“你自诩清高,你孤傲,你超然,你能够真的一点也不食人间烟火吗?与世隔绝吗?身居闹市如在深山吗?”
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理想与俗世生活割裂的问题与困境,从“五四”起就是作家们力图通过文学形象来反思、呈现的。鲁迅曾在《伤逝》《幸福的家庭》中将小知识分子从理想的云端拉回到现实的地面,他正视知识分子如常人一样也有此在的、甚至是肉身的需求,难免需要面对琐碎而现实的生活。鲁迅在百年前就解构了“战士”“全部可歌可泣”的神圣化形象,还原其与生命此在相关的日常样态,建构起“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实际上的战士”形象。一百年后,鲁迅的思考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可是,从一百年前的“实际上的战士”到一百年后的“真正的艺术家”,这其中思考的轨迹是什么?我想,冯骥才以纯粹的艺术精神来唤醒过度沉溺于俗世生活的艺术家们,但却走向了二元对立的另一端,消弭了俗世的合理性,甚至对家宅空间中的“诗意”被“实用”赶跑而怅然、心痛不已。谁是艺术家?他的“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社会生活部分的缺失,会将艺术引向何方?“从艺术家的生活和实践来看,艺术家——作为一个社会的人——的理想并不等于艺术理想,艺术家的需要和追求也并不仅仅是艺术需要和艺术追求。把艺术创作活动从艺术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剥离出来,就会导致把主体从中实现同对象世界的现实联系的那种内容丰富的过程抽象掉。而这种主体同现实联系的丰富过程——即生活、实践,对于艺术创作又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不仅是艺术作品内容产生的源泉,而且是艺术创作动力产生的源泉。”艺术家是社会的人,是多维立体的人,艺术家的理想、需要、追求也是多维的。当艺术家被从现实生活中剥离出来,仅存艺术的单一维度,我们难以想象其艺术的感觉、激情、灵感、冲动缘何而起;失去了他重要的观照对象、表现的镜像,艺术创作的源泉是否会走向虚无与枯竭?我们看到,云天几次获得创作的灵感都是发生于对山川大河的巨大震撼。不可否认,离开了大自然的艺术家是孤独的,缺少感动和净化的,但隔绝于生活的艺术创作将会如何?洛夫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模仿、新奇形式的追逐中背叛了纯粹的艺术,精神“出轨”,走向创作的危机,作家宣判了他灵魂与肉体的死亡。而這又何尝不是脱离真正生活实践的艺术危机呢?
四
“美,不就是精神的浪漫吗”,可以说是冯骥才赋予艺术家的精神气度,也是贯穿于文本全篇的叙事声音、调性与风格。近八十岁的冯骥才,以上世纪七十年代历史节点为“出发地”,以“七十年代”的精神复原为旨归,让历史的链条在叙事中完成了衔接,力图为当下的艺术及艺术家们注入往昔的理想主义精神。如此叙事的立场和逻辑起点,让作家的整体叙述姿态也进入到自然、纯然之境。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冯骥才对技巧的运用,一切都是经过他情感之网的过滤与筛选,在自然而然中发生、流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艺术家们》兼具虚构与非虚构的性质。非虚构的情感与体验,支撑起了虚构的叙事。或许,不见策略的策略是于“回忆录”“心灵史”之作而言的最佳选择。这部作品于冯骥才而言,绝非是普通“创作”那样简单,它沉潜到历史与现实的深处,也前所未有地融入了作家自我个体的经验、情感、生命,是他凝聚、蕴蓄了大半生的心力谱写出的灵魂音符。在叙事中,他绝不掩藏自己的声音,将自己的经历,对艺术的理念、追求,对艺术家的判断、期待,对爱情的体悟,对友情的理解,对社会时代变迁的思考、内心的冲突等等,不断传递出来:“然而物质的损毁可以重构,心灵的缺失无法弥补。”“对自己失去自觉的人是另一种死亡。”“真正的朋友不是为你弹歌相庆,而是在人生的岔道上帮你看清去处。”“一个社会没人关心知识分子问题才是一个大问题。”……文本中随处可以听到发自冯骥才内心的声音,他将自己多年来对存在世界与艺术世界的认知、思考、困惑和盘托出。
文本阅读中,我们感受到他创作《艺术家们》时那种沉积、孕育了几十年的激情与思考、“我要表达”的热烈与冲动。他将文化遗产抢救的激情惯性带入到“返归”的文本世界。“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冯骥才为这句诗做了最形象、最生动的诠释。为此,他扭转自己在《神鞭》《三寸金莲》等文化小说中的理性思考、深度剖析的风格,也与多年来流行的“零度写作”断然作别。我想,这也许就是冯骥才叙事的现实意义所在,他是在以最朴素的叙事的形式与路径,完成对艺术家也是更多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引领、净化,与有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形成“互文”,呼应他前期小说创作文化题旨的深层思考。
我们能够感受到,冯骥才面对艺术之谷高声疾呼的声音是如此响亮,叙事中来自作家的大量声音交织成可以成像的细密的波长。他就是要以《艺术家们》的叙事灯塔,照亮这个被庸俗化了的艺术家们的心灵和他们驻足的世界,在时代的青铜雕像上镌刻下一个老艺术家的声音。“《艺术家们》是冯骥才的心灵史,也是他的谈艺录,对于当代社会或艺术界未尝又不是一部启示录,这里面,显然有他的很多忧思。”应该说,冯骥才的忧思,直指我们时代艺术家精神“缺钙”的病症所在,开出以“忘我精神”“牺牲精神”强壮肌体的诊疗药方,抵达超越艺术本身的精神至境。这是对艺术的呼唤,也是对时代的召唤。一部《艺术家们》,其生成的启示意义与价值其实已超越了冯骥才蕴蓄多年的思考和叙事表达本身,它不仅指向“谁是艺术家”的多维命题,也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突出重围、实现自我精神守望的“历史镜像”。小说结尾“他的老屋可是真正在衰老了”是否再一次以空间隐喻的方式,昭示云天式艺术观已然老去,需要不断“维修”寻找新的支撑?云天与隋意最后的那段对话:“我把昨天给你带回来了”“你给我带回来的,还有明天”,是否是老艺术家不仅守住昨天,也是对充满无限可能的明天的憧憬?我们看到,在文本悠然不尽的开放式结尾中,人物与冯骥才一道为真正的艺术家塑形、为美好的未来构筑精神愿景。我想,这才是这部《艺术家们》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吧。
(作者单位: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