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显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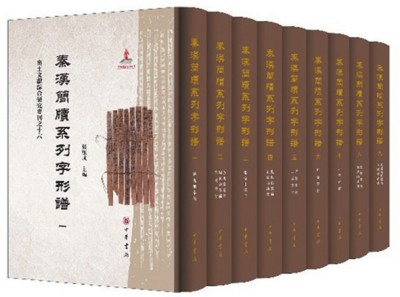
《秦汉简牍系列字形谱》(全十册),张显成主编,中华书局2024年6月第一版,1680.00元
出土简帛文献以其独特的形式承载着古代文明的密码。这些出土的简帛,不仅是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的宝贵资料,更是汉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活化石。它们为现代学者提供了一扇窥探古代世界的窗口,让我们能够更真实、更直接地触摸到历史的脉搏。而全面清理秦汉简牍文字形体,不仅对汉字史、汉语史、书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简帛的整理研究以及与简帛相关学科的研究同样至关重要。
最新出版的《秦汉简牍系列字形谱》就是一部系统整理秦汉简牍字形的创新之作。本书是对2016年6月之前已刊布的大宗简牍文字的集中整理,包含15种分谱,其中秦简字形谱4种(《睡虎地秦简字形谱》《放马滩秦简字形谱》《周家台秦简字形谱》《龙岗秦简字形谱》),汉简字形谱11种(《张家山汉简字形谱》《凤凰山汉简字形谱》《孔家坡汉简字形谱》《尹湾汉简字形谱》《武威汉简字形谱》《居延汉简字形谱》《居延新简字形谱》《敦煌汉简字形谱》《额济纳汉简字形谱》《武威汉代医简字形谱》《东牌楼汉简字形谱》)。其整理编制方式既注重吸取前人的经验,又注重避开前人的不足;既具很强的学术性,又有较强的实用性。可供古文字学、简帛学、历史学、普通文字学、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案头使用。
本书从编纂到出版,历时二十载,其中的艰辛与挑战,自不待言。趁此新书付梓之际,我们采访了本书的主编,文献学与语言文字学专家、西南大学张显成教授。
问:全面清理秦汉简牍文字形体,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不仅需要深入挖掘和整理大量的出土文献,还要对每个字形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那么,是什么驱动您和您的团队投身于这样一项艰巨的工作?
张显成:秦汉时期,汉字的形体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据出土文献资料显示,到了西汉晚期,隶书的演变已经完成,例如武威汉简已经展现出成熟的隶书风格。进一步地,到了东汉末三国时期,楷书已基本成熟,如三国吴简已经接近楷书,尽管部分字的横画还保留了一些隶书的特点,即所谓的“蚕头燕尾”。到了西晋初年,楷书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面清理秦汉简帛的字形,对于我们理解汉字的发展脉络、书法艺术的演变以及文化历史的传承,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有鉴于此,我很早就有全面清理秦汉简帛字形的计划,2004年便带着研究生陈荣杰试着对武威汉简字形进行汇编,当时称“武威汉简文字编”。我们把2016年6月以前已全部刊布的简牍,都纳入编纂范围。原本计划也一并编纂帛书字形谱,后来得知复旦大学刘钊先生的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王堆汉墓简帛字词全编”将编纂字编,就放弃了编纂帛书字形谱的打算
问:确实,“文字编”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称呼。在一定范围内 对汉字字形材料进行整理编纂,展示多变的汉字字形,我们一般称其为“文字编”。比较经典的文字编比如《甲骨文编》《金文编》等,都是语言文字研究和书法研究的必备工具书。然而,对于这部 系统整理秦汉简牍字形的成果,为何选择了“秦汉简牍系列字形谱”这一名称,而非传统的“文字编”? 在这里,“字形谱”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字编”有何不同?
张显成:学界多称字形汇编成果为“文字编”“文编”,比如你提到的《甲骨文编》《金文编》,又比如陈松长的《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或者称“字形表”“字表”,比如徐中舒的《古文字字形表》,《侯马盟书》所附的《字表》。我前面也提到了,我们在一开始对武威汉简字形进行汇编时也称其为“武威汉简文字编”。但是随着此项工作的深入和经验的积累,我们认为,在编纂字形汇编时,应当对已全部刊布的简牍逐批进行清理,不光要清理每一字的形体,将不同的代表字形按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有机排列,而且还应当清理每一字出现的频率,全面反映所编纂材料字形全貌,构成字形谱系,所以我们称自己的字形汇编成果为“字形谱”。我们的字形谱,每个字形都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字头的阿拉伯数字编号,从“1”开始,最后一个字头的编号就是本字形谱的字头总数。编号下面就是按大徐本《说文》顺序排列的字头,字头下则是这个字头所对应的小篆。然后是这个字头字在所编文献中出现的次数(即字频),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清理出每一个字出现的频率。这是我们的“字形谱”独有的,区别于其他“文字编”的最大特点。这种标“字频”的做法,是在我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字形全谱》一书中第一次采用。每一个字头都标注字频,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揭示所编文献的用字分布情况,揭示出极高频字、高频字、中频字、低频字,以及一见字(仅出现一次的字)的情况,这对于汉字用字史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把同时代不同性质简帛的字频分布情况进行对比,或者把不同时代同性质简帛字频分布情况进行对比,就会给我们提供很多宝贵信息,对于汉字史的研究意义自不待言。当然,要做好这一工作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你得首先正确释读简文,然后根据字编的字形入编标准,确定每一个字的出现的字数,我们的入编标准是字形基本完整可确释者方入编,所以,要标注每一个字头下的字频,不是用WORD文档一键就可统计出来的。字形谱的字频之下即是代表字形。这些代表字形按照先排规范字形,再排欠规范的字形的原则排列。在每一字形下,都列出相应的出处和辞例,方便核对。
问:采用字头下标注字频的做法无疑体现了 本书的创新之处。而文字汇编类的成果,最关键的,首先是对文字的释读。请问本书在这个方面有什么特点?
张显成:文字汇编成果,首先要尽量解决文字的科学释读问题,而简帛文献的释读,常常是个无底洞,因为有很多字形不见于传世文献,而且简帛文献是无数书手写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书手的书写习惯书写风格各不相同。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整理者释读成果基础上,在广泛吸收斟酌学界有关释读成果的基础上,尽量正确释读简文。对此,我们深有体会,例如《武威汉简》的《特牲》48简第5字,整理者释文和后出的张德芳先生主编、田河著《武威汉简集释》释文均作“”,我们细查图版,此字作“”,最下面实际上是“巾”的省笔,不是“口”,是省去了中间一竖,如果是“口”,则找不出理据,因此这个字应当隶作“”,是“幕”的省笔俗写异体,所以我们将此字置于字头“幕”下,处理为“幕”的异体。再如,《敦煌汉简》1448简整理者释文“存贤近圣,必聚谞士”的“必聚谞士”很难理解。整理者所释的“聚谞”二字的图版作“ ”,我们在吸收学界有关释读成果的基础上,释此二字为“听譋(谏)”,这样,“存贤近圣,必听谏士”就很好理解了,文意也顺畅了。当然,尽管我们下了大功夫来释读简文,但还是不敢保证没有释读问题,也希望学界共同努力来促进简帛的科学释读。
问:自2004年起,您的团队就开始着手进行秦汉简牍文字的字形汇编工作,直到今年2024年,《秦汉简牍系列字形谱》才得以问世,这个过程历时长达20年之久。我想请问,在这么漫长的编纂过程中,您认为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部分是什么?
张显成:在编纂过程中,最花时间和精力的是对字形的处理。文字汇编类型的成果,最重要的就是收录字形的准确与清晰。我们的字形处理工作是从简牍的整理报告开始的,这些报告都以照片形式呈现,而简牍字图往往带有底色,有时底色还非常浓重。因此,对于我们计划收录的字形,首要任务就是使用计算机软件进行脱底色处理。这个过程既要确保字形的笔画清晰可见,又要保证字形不失真,真实地反映出书写时的原貌。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巨大,尤其是一些复杂的字形,处理起来特别耗时费力。通常,处理一个字至少需要二三十分钟,而一些难以处理的字形可能需要四五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整个字形处理的时间占据了我们字形汇编总工作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由于长时间整天处理字形,握鼠标的手经常会肿胀,辛苦程度可想而知。我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字形全谱》的《后记》中曾经提到:“编制字形谱这一类工作,是聪明人不做、笨人做不了的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愿意投入这项工作,因为它对于学术 研 究 具 有 重 要的价值。此外,在编纂过程中,原本有些分谱已经完成,但后 来由于又刊布了更为清晰的图版,我们便舍弃了原来已处理好的字形,而使用新图版来重新进行字形处理。比如分谱之九《武威汉简字形谱》,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是最早进行编纂的,早已完成,原来的入编字形是据1963年文物出版社的整理报告《武威汉简》图版来进行脱底色处理的,但2020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张德 芳 先 生 主 编的《武威汉简集释》,所刊彩色照片 比原来整理报告清晰,因此我们果断舍弃了原来的字形,利用新刊的彩色图版重新进行字形处理。这无疑加大了工作量,但却保证了字形的准确与清晰。类似的情况在《龙岗秦简字形谱》《居延新简字形谱》《武威汉代医简字形谱》这三个分谱中也存在。
问:在大著问世之际,请问您认为在编纂过程中留有什么遗憾?
张显成:遗憾是一定会有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有些分谱因为已公布的简牍图片不够清晰甚至很不清晰,导致对于字形结构笔画的判定难度很大,字形处理也比较困难。比如放马滩秦简,出土时就质量欠佳,相关整理报告的图版也不够清晰,能达到入编字形谱标准的字形就比较有限,从而《放马滩秦简字形谱》的入编单字就相对少一些,让人遗憾。二是我们编纂的范围是2016年6月以前已全部刊布的简牍,而现在2025年了,这9年间,又有很多重要的简牍陆续刊布,比如肩水金关汉简、悬泉汉简等。这些2016年6月之后才刊布的简牍的文字汇编工作,就只有留待日后为之或学界来共同努力了。三是我们于字头下凡见于《说文》的字,均出示《说文》小篆,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读者与《说文》对照。我们所据的小篆是通行的大徐本《说文》小篆,但大徐本小篆本来就有问题,例如,索,大徐本作“”。 ,大徐本作“”。,“从,索声”,按理小篆当作“”方与“索”的小篆“”统一,显然大徐本“索”“”二字的小篆字形是自相矛盾的。但我们的字形谱的体例是准于大徐本的,故只得按大徐本出示小篆,实为憾然。
(本文采访者徐真真为中华书局副编审)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