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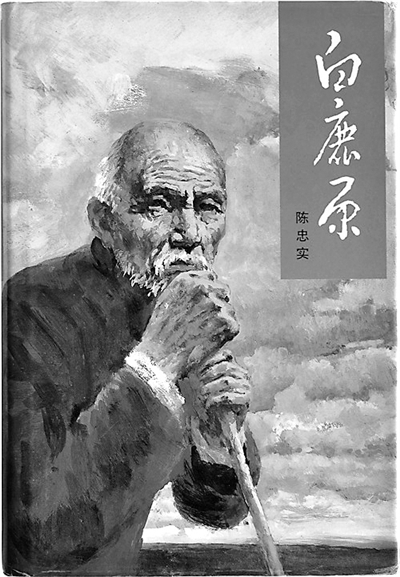
陈忠实爱吃面。写《白鹿原》时,在远离闹市的乡村祖屋里,不知吃了多少媳妇亲手擀的面。凭着这部“垫棺作枕”之作,一跃成为当代文学史绕不开的人物后,他还是爱吃面。有评论家说,《白鹿原》也是这样一部有“面性”的作品,“像陕西媳妇揉面一样,揉啊揉,揉得不能再筋道了才算完”。
《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与1993年第1期发表了《白鹿原》。1993年6月,作为图书单行本,《白鹿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25年了。期间,《白鹿原》斩获茅盾文学奖,发行200余万册,并被改编成话剧、电影,以及最近备受好评的电视剧。
《白鹿原》撼人心魄地讲述了陕西关中大地白鹿两家的兴衰史。从清末民国一直到解放初期,横跨数十年,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悲剧和历史演变,以其雄浑凝重、咄咄逼人的气势,深沉冷静的历史思考以及众多崭新饱满的艺术形象征服了读者。可以说,《白鹿原》不只是陈忠实自己的,它属于所有读者,它是我们共同的《白鹿原》。
“成了!咱不养鸡了”
“这是1988年的清明前几天或后几天,或许就在清明这个好日子的早晨,我坐在乡村木匠打制的沙发上,把一个大16开的硬皮本在膝头上打开,写下《白鹿原》草拟稿第一行钢笔字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删简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的眼前,也横在我的心中;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陈忠实曾这样拣拾起写作《白鹿原》的那个原点。当年他已经44岁了。
其实,写《白鹿原》时,陈忠实的心情非常复杂,生活也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娃上学快交不上学费了。我给老婆说,我回原上老家去,你给我多擀些面带上,这事弄不成,咱养鸡去,养鸡为主,写作为辅;事弄成了,咱写作为主,养鸡为辅。”这段典故,陈忠实多次讲起。
“我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开会,路遥发言,李星绕到我的后面耳语:‘今早听广播,《平凡的世界》评上茅盾奖!你年底要把那事不弄成,干脆从这楼窗户跳下去!’”路遥的获奖,极大地激励了陈忠实。1991年,整整写了6年的《白鹿原》终于完成。李星来到陈忠实家,把50万字沉甸甸的书稿往床上狠狠地一甩,说:“事咋叫咱给弄成了!”
1992年的一天,陈忠实回西安的家背面背馍,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贤君的回信,一下子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惊叫了几声,哭了,爬到沙发上半天起不来。老婆慌了,问“出啥事了,出啥事了?”他说:“咱不养鸡了!”
往返于成功与失败之间
在大多数人眼中,《白鹿原》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无可挑剔,攀登欣赏就好。但在陈忠实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生张高领却对《工人日报》记者说,《白鹿原》让陈忠实处在成功与失败之间。
1991年末,面对即将完成的《白鹿原》,陈忠实却对它“能否被理解、被接受”忧心忡忡。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陈忠实才如释重负,敢于发表这部小说。
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中说,按照他原本的设想,《白鹿原》要写上下两部,每部大约30万~40万字。然而,由于当时出版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不再拨款,自负盈亏,“读者群决定着一本书的印数和发行量”。所以,考虑到“这本书未来的市场”,陈忠实决定将篇幅压缩至40万字左右。他还从擅长的“白描语言”转而寻找一种“形象化的叙述”,即“叙述语言”。为了实现这一自觉的语言实验,陈忠实先后创作了《窝囊》《轱辘子客》《害羞》和《两个朋友》,从而实现了语言风格的剧变,像简洁明了的海明威一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
作品付梓之后,我们亦可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上享有巨大声誉,不仅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还被学术界视为一部“史诗”“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另一方面,也饱受非议:评论家南帆认为其叙述话语是破裂的,叙述结构是脱节的;评论家袁盛勇批评《白鹿原》“由于指向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简单认同,因而没有提供任何创造性或者说具有原创性的观念”;评论家宋剑华批评它是“一部杜撰历史与发泄情欲的‘拼凑故事’,获得茅盾文学奖“反映了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沉沦的衰败之相”……
我们该如何读《白鹿原》
提及《白鹿原》,无论是小说、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历史风云中白鹿两个家族的兴衰成败与恩怨情仇,无疑很引人注目。显然,在各种艺术形式的《白鹿原》中,家族故事往往是最精彩的。然而,对这部分的理解也最容易流于浅俗。
在张高领看来,白鹿两家与其说是两种家风、人格或信念的对决,毋宁说是关于白鹿原未来何处何从的追问。鹿子霖、鹿兆鹏、黑娃和白灵都是现代的代表,无论他们初衷是什么,但在白鹿原落地生根的过程中无法因地制宜,导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而白嘉轩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化解任何外来势力对白鹿原的粗暴干涉,为乡民撑起一方安生立命的晴空。在此意义上,《白鹿原》重构了中国当代文学对农村历史命运的新想象。
面对“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被现代”似乎是农村无可逃避的历史宿命。然而,《白鹿原》却试图颠覆上述叙述,否定现代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以儒家文化重构另一种乡土秩序。《白鹿原》对现代政治的乡土治理提出了批判性理解,它的核心问题意识并不在于儒家文化,而是如何在“革命”叙述与“启蒙”话语之外,寻找另一种乡土治理的可能性。这或许是《白鹿原》的最深刻之处,正由于此,乡约族规、族法族谱、祠堂书院都别具深意。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
和很多人一样,张高领认为《白鹿原》中最能打动他的人物便是主人公白嘉轩。
陈忠实曾说:“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很显然,白嘉轩是陈忠实最着力、最精彩也最具理想主义的人物形象。某种程度上说,理解白嘉轩是理解《白鹿原》的关键。
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是白鹿两族的族长,同时也是一位乡绅地主。在此前的文学叙述中,无论是族长还是乡绅地主,往往是负面的,而白嘉轩的出现改写这一历史图景。白嘉轩对儒家文化坚信不疑,身体力行,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维持着白鹿原的生活秩序,这一悲壮的人物形象颇富感染力。在白嘉轩的主持下,借助《乡约》和祠堂,白鹿村不但克服了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现代事件带来的冲击,而且重铸了一个儒家文化的乌托邦:“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蔼可亲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
虽然白嘉轩最终不得不关闭白鹿祠堂、不再过问族中事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反而更加磨砺了他至死不渝的决心,在他看来,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错的是那个兵荒马乱、鸡飞狗跳的时代。毫无疑问,白嘉轩对现代性事物的拒绝与否定并非无的放矢:无论是鹿子霖代表的国民党、鹿兆鹏所代表的共产党,还是白灵所追求的女性解放,作为现代的产物,它们在白鹿村落地生根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南辕北辙式的错误,在这一点上,白嘉轩的不合作态度未尝不是一种无声的批判。毋庸置疑,白嘉轩失败了,但仍不失为失败的英雄。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