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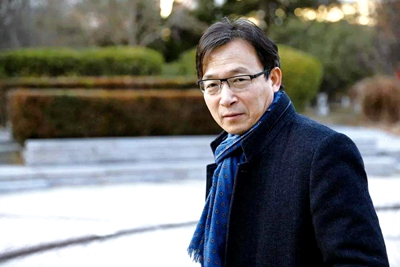

记 者: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体量庞大、内容驳杂,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可能有很大的阅读“难度”。您如何评价《应物兄》的文学价值?
王本朝:在某种程度上,它的获奖不仅是对文学成绩的肯定,更是对文学探索及艺术多样性的鼓励。如果将时间跨度往前后移动下,它不仅是最近几年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还是一部丰富而独特的小说,其影响日后会逐渐证明出来。的确,《应物兄》的体量庞大、内容驳杂,对普通读者阅读起来有“难度”,我估计它不会成为大众畅销小说,但会进入文学史,成为文学经典。
在艺术上,小说既有“史传”传统的风韵,又有先锋小说的特点。小说叙述也取杂语体,旁征博引,既机锋有趣味,又冗杂显拖沓。不仅如此,《应物兄》的叙事视角也颇为复杂,表面上看是同一人物,实际上也是分裂的,容易迷惑人。它的故事完整,人物独立,亦真亦幻,似真又假,写实性隐藏寓言性和象征性。
杨 扬:的确,这本小说不是一本随便就能“悦读”下去的作品。小说写得很密实,与他的《花腔》相仿,有着非常细密的文字关联,每一页之间,都难以跳跃过去。70多万字的小说,要这么一页一页密不透风地读下来,真是一件折磨人的事。但从专业的角度,有些书不一定好读,但还得认真对待,《应物兄》就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当代中国小说经历了诸多变化,到了今天很多路数大家都熟悉了,见怪不怪,但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小说写作依然需要有一些新探索,这些变化不是单纯形式技巧方面的实验和尝试,而是包括生活体验在内的小说艺术的综合改变。在我看来,《应物兄》中的人物、场景,换一个别的身份的人物或场景,也末尝不可,重要的是作品提供给我们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它让你觉得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时代质感。
记 者:《应物兄》中有这样一句话: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深刻而沉重地将代际问题带入时代话语的讨论中。您对于小说内部隐藏的代际反思与历史疼痛,有着怎样的理解?
王本朝:《应物兄》依“应物象形”目标,为上世纪90年代后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精神状态、文化心理画像、作传。它是写实的,也是象征的。它的故事并不复杂,主要以济州大学筹建儒学院,联系儒学大师程济世归国及其与相关人物周旋的应物兄为叙述中心,将他各种人物的打算、想法以及冲突、矛盾汇集于儒学复兴,由此带出知识人的历史和现实、名誉和利益、欲望和心理等复杂关联,既信誓旦旦、众声喧哗,又一地鸡毛、鸡零狗碎。有意义的悲喜剧与无意义的荒诞反讽都相互纠缠。说它是知识阶层人物的博物馆,是一部百科全书的小说,都将其平面化了,它的意义应该在于思想的深刻和艺术的创新。
杨 扬:应物兄不是上世纪80年代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那个充满忧患的知识分子了,也不是90年代格非《欲望的旗帜》中有点颓唐的知识者形象。应物兄属于今天这个时代,带有这个时代的各种气息。他焦虑,但已超越了那个为衣食而忧的阶段,是一种温饱之后的后焦虑状态。他不是单纯的事业至上者,为了情爱和欲望,甚至连名誉都愿意抵上。他熟悉熟人社会人情世故,周旋于社会名流之间,但也不是你好我好的江湖中人,他有时会偏激,像个性情中人,出离于熟人社会的江湖游戏。他看似君子,但细看又不像,他在校园内外台前幕后跑上跑下,好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忙碌的人,但没有人真的把他当个人物看待。应物兄的忙和他的闲,都是我们时代生活的映照,但不是镜子式的。对于小说而言,最紧要的是这个时代所有的痕迹,李洱都想方设法在作品中有清晰或不清晰的表现。就这一点而言,我感觉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做到的。
记 者: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叙述中,对于知识分子形象和命运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谱系,您认为《应物兄》作为书写知识分子群体的作品,有什么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王本朝: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单纯透明的,尤其是到了现代社会,现代性即矛盾性,是驳杂而分裂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更是这样。对这一群体的书写是一种挑战,看别人容易,要看清楚自己,难。有关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和命运谱系的作品,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鲁迅《孤独者》《伤逝》,喜欢钱锺书的《围城》,上世纪80年代后的小说,贾平凹《废都》、阎真《活着之上》以及李洱《应物兄》等都是有力度的优秀之作。
李洱写知识分子很到位,没有在外面写,而是深入知识分子内里。他有真切的感悟和体验,也有深入的思考和思想。他写的是生活、是生命、是心理、是文化。他把知识分子时代化、细节化、知识化,他用了知识分子语言写知识分子,用知识分子文体写知识分子,用知识分子风格写知识分子。这就是他的成功。
更重要的是,这一作品的获奖对于今后的当代文学书写有着典范意义,既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又要直面生活、挑战生活;要力求有思想深度的写作,写出有艺术创新的作品;要在快速时代改变用力方式,调整心态,力求慢生活,慢写作,以作品质量取胜,写出艺术精品。
杨 扬:与那种将大学教授定义为知识分子的创作套路不同,李洱是带着反讽和自嘲的姿态来观照人生。或许他在《花腔》中处理知识分子与革命关系时,对知识分子视死如归的精神境界充满了敬意。但对于今天的人生,他的坚定性变得有点复杂了,毕竟《花腔》是他而立之年的创作,而《应物兄》是年过50之后的奉献。对于小说家而言,或许会有一种回不去的悲哀。但反过来讲,有时这种复杂含混,甚至某种调和,恰恰是作者洞悉人性之后的一种无奈和解嘲。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