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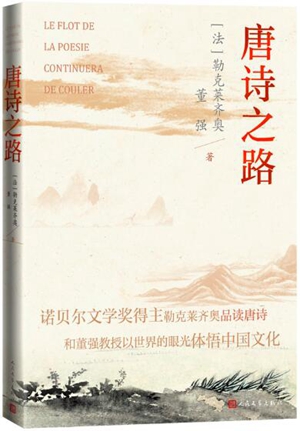
《唐诗之路》,(法)勒克莱齐奥 董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唐诗之路》是翻译家董强与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合作的。这种合作,按勒克莱齐奥所说,是友谊的结晶,他们一起挑选了这本书中的诗作。实际上《唐诗之路》的主体内容由勒克莱齐奥所著,董强则在书中撰写了一篇长文,题为《镜·塘》,介绍他们之间的相识、交往,以及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与法国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董强曾在巴黎留学,先住在拉丁区的一个阁楼上。屋里有一张小学生课桌大小的桌子,就是他的书桌。在这张书桌上,董强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是法文的。也正因此结识了勒克莱齐奥——这位已经拥有非凡荣誉与影响力的法国大作家,开始了他们持久的源于文学而来的友谊。毫无疑问,勒氏热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热爱唐诗。他阅读了许多翻译至欧法地区的中国古代典籍,包括古典诗歌,并多次来中国讲学、交流、旅行,探寻李白、杜甫等诗人的足迹。这使勒克莱齐奥对中国的了解认知从观念、想象深入至大地、历史,以及具体的人群之中。这种研究与了解强化了他的热爱,并决定与董强一起写一部关于唐诗的著作。按照董强的介绍,勒氏对中国文化的钟情,源自其少年时代。而他对唐诗的理解,很快就突破了西方传统的“路径”与“视窗”。那么,作为一位法国作家,当勒克莱齐奥说热爱中国文学的时候,究竟是从怎样的角度来欣赏这些诞生在遥远国度的古典诗歌呢?
以我的观察,勒氏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应该是从时间的历史长度与空间的世界范围展开的。他在《唐诗之路》的序言中指出,“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感到同那个时代的诗人和艺术家是那么的近,我们能理解他们,那个时代与我们的时代是如此的相似。”这就是说,即使是今天生活在欧洲的作家,也仍然能够与千年之遥的亚洲大陆的诗人具有相同的情感。这种情感由诗歌而得以沟通、连接、融合。勒克莱齐奥强调,没有比唐诗更加不“古典”的诗歌了。正是在中国唐朝,抒情性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它一方面满足了中国思想、中国道教对均衡与和谐的追求;另一方面,它向多义性,以及情感的丰富性开放,让情感发出无穷的回声。可以说,勒氏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唐诗的某种秘密。他认为:“中国唐朝的诗人们,是后来文学中发明的许多东西的先驱。”这一评价至关重要,是许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尽管勒氏并没有详细分析这种“先驱性”是如何体现出来的,但他仍然列举了从意大利文艺复兴诗歌、法国“七星诗社”的创作,乃至拜伦、雪莱、缪塞的浪漫主义诗歌作品等来说明。这种在世界范围中进行的研究,使我们对唐诗的了解有了全新的感受。而勒克莱齐奥更强调,唐朝在中华文明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它是艺术上完美的榜样。当人们谈到唐诗的时候,往往会想到它的古典,但勒氏认为这应该是一种革命,“是一种现代性的诞生”。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中国表现出不同于其它国家、地区文明的特殊性。人们难以用通行的标准、概念、理论来简单地对中国进行界定。就一般意义的现代性而言,主要是指欧洲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向工业化的转型。但是,在中国,许多属于“现代”的东西早已出现,并成为了“古典”。勒克莱齐奥认为中国在唐代,“诞生了一种真正的个体思想,也就是一种自我觉醒,一种自由的表达,以及自我仲裁的自由。”勒氏所说的这种自由,不仅表现在诗人的精神世界中,还表现在诗人对语言,具体而言是中国古代汉语及其语序的“颠倒、分割,或重新调整”等方面的“自由”运用上。他认为只有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才“允许这样的自由”。
人的觉醒是现代社会到来的基础。当人从神权的控制中解放之后,现代社会才蹒跚而至。但是,董强认为:“重要的不是去指出唐诗的‘现代性’,而是要显示其永恒性或超越时间性。唐诗是永恒的。这也许才是它的真正的力量:它肯定比我们现代人还要活得更长久。”这种永恒性或者说超越性就是说,唐诗所创造的艺术并不属于哪一个具体的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时代,以及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域。概括来说就是,唐诗是属于人的时代。只要人类存在,唐诗的意义就不会磨灭,就会熠熠生辉,被永恒所永恒。
在《唐诗之路》中,勒克莱齐奥用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李白。毫无疑问,李白是他最喜欢的诗人,或者说之一。当勒克莱齐奥第一次读到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时,被诗所创造的意境所震撼——不仅仅是感动。他甚至立即起身,往距离作家生活的城市法国尼斯不远的瓦尔山谷,去体验诗人在诗中表达的境界。后来,甚至在毛里求斯南部的摩尔纳火山岩前面再一次体验这种感受。“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对照互认。他们在这样的对应中发现了自己并消泯了自己,进而融为一体。在这里,大自然与人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心灵世界。在李白众多的诗作中,《独坐敬亭山》并不是最具影响力的,但就这首诗所营造的意境而言,却是非常典型的。勒氏的感受敏锐非凡。他极为自然地抓住了这首诗最重要的特征,并指出,“在诗歌面前,李白一直都是谦卑的。他从未认为自己比大自然中的各种元素更为优越。相反,他表达自己对无垠天空的臣服,对高山、森林、河流的臣服。”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大自然是永恒的主题。即使是那些并不以表现自然为主的诗歌,也难以脱离自然,往往把社会生活、人生境遇、爱情战争等与自然统一起来,融为一体。勒氏列举了许多诗人的作品,包括杜甫、李商隐、白居易、王维、杜牧等等。他们在大自然中寻找感悟到了自己存在的根本,并将社会生活与自然统一起来。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反映。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作多以对社会生活的表现为长。但是,在杜甫的诗歌中,大自然也从不缺席。即使是诸如《兵车行》《石壕吏》这样的正面描写现实生活的诗作,也有“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百草”“青海头”这样的自然物象是诗人情感的形象化表达。
勒克莱齐奥从这样的一体融合中发现,或者说感受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审美魅力。他指出,“在唐朝诗人那里,大自然更加亲密,更加真实。诗人们并不利用大自然,而是被大自然所驱动。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充满美感和奥秘的世界,创造出了人的情感。”中国传统诗歌的这种审美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方式有着极大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将“道”作为思考问题、解释问题、处理问题的原点、核心、基础。人与社会具有区别于宇宙自然中其它存在的特性,但又具有与宇宙自然相通的普遍性,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的这种普遍性。道不仅是对宇宙自然法则的表达命名,亦是对其存在的规定。这种规定也会体现在人的行为及其社会生活之中。同样也会体现在诗歌艺术中。那些优秀的诗歌总是能够表达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致性、相融性、互现性。它们相互证明、相互表现、相互统一。
勒克莱齐奥虽然是生活在法国的作家,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下了很多功夫,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也非常熟悉。如他曾经研读过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著作,对道家思想有非常深刻的体悟,对佛教、道教的基本理念也有深入的把握。他也熟悉中国历史的基本演进,以及在不同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活跃在那一时代的诗人、作家、艺术家。董强说,作为对西方现代文明怀有质疑的作家,勒克莱齐奥一生寻找欧洲文明之外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墨西哥文明都是他从内心深处向往、钟情已久的文明。正是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勒氏日渐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尤其是对中国诗歌的热爱。在《唐诗之路》中,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中来分析唐诗的意义,认为唐诗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文化传统,又开启了宋及其之后的文化传统。他了解道家、道教,能够运用其中的美学思想来认知唐诗。比如他强调道家中“灵感”现象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意义。认为“唐朝的诗人同时也是书法家,形式的创造者。有时,哲学的气息会穿过他们,揭示存在的秘密,以及现实的狂醉。当唐诗之路终结,中国的思想成功地与道的光辉相融合”。
这种对不同文化的深入了解使勒氏具有了一种与一般人截然不同的敏锐性。他能够非常准确地感受到中西或者说中法诗歌之间的异同。他举重若轻地梳理了唐诗在人类诗歌历史中最为突出的贡献;他形象地比喻由于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建立在暴力的侵占上,不围绕固定的中心、没有稳定的结构,也不建立在哲学与道德的法则之上的帝国,以及与之对应的中华帝国,“不论是唐朝,还是清朝,都是一个坚固的建筑”。这当然也影响了中国的诗歌。“在整个历史中,中国通过其诗人和哲学家的声音,重申了人的绝对崇高地位,人享有正义和平等的权利。”他认为,这种现实的思想从未否认过想象、幻想、神话和虚幻的可能性,但总是使它服从于智力的清晰性和理性经验的必要性。“这正是唐诗的现代性。”
董强与勒克莱齐奥走在了不同的出发点却相向而行的道路上。董强作为一个在中国读书成长的学者,更多地接受了东方的文化,又在巴黎留学,研究了欧洲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他在书中介绍了欧洲,尤其是法国学界对中国之研究、了解与热爱,亦比较了东西方,特别是中国与法国文化之间的异同,指出“中法的诗歌之间,存在一些隐秘但共同的路径,值得我们去探索”。他借用凡尔赛的镜厅与北海公园的镜清斋进行对比来指出中法之间审美的一些“本质差别”。他认为勒克莱齐奥的高度,“在于将唐诗作为一种全人类文学的黄金时代,放置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峰”。勒克莱齐奥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文学高峰,除荷马史诗外,还有阿兹特克文学、波斯文学,以及属于西方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莎士比亚与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而在中国,则是唐诗。董强说:“放眼望去,唐诗是人类文学最高峰之一,而且在时间上,除了荷马史诗之外,远远高于其他几座高峰。”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在一个生活在当下的法国作家眼中,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唐诗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崇高地位。勒克莱齐奥在他的序中说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诗词的力量:可以在任何时代,任何场合下阅读。只需轻轻吟诵,就可以进入一个另外的世界。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