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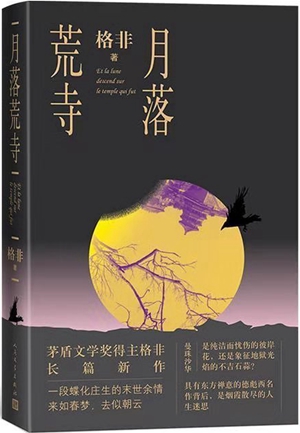
《月落荒寺》,格非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月落荒寺》并非格非的大部头,但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能看到格非近年来思考的母题。小说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婚后的庸常处境:妻子出轨,婚姻破裂,自己和儿子处在难解的尴尬中。主人公林宜生是卷入商业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写照,他是苏州人,在南京学习10年,然后北上,成为北京一所理工科大学的哲学教授。受益于市场经济和国学热,他在各地讲课,收入和地位跃升,名也有了,利也有了,可却仍感到虚无,尤其是在妻子与白人派崔克出国、儿子不服管教后,他走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感受到无力和彷徨。
《月落荒寺》要写什么?我想,一篇关于格非的采访提供了线索。在《上海书评》刊发的《格非谈〈江南〉内外》中,格非说:“实际上我当年部分参考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讨论的‘常人’——海德格尔将其定义为‘无此人’。很多人活着,但并不存在。存在是我们的最低目标,也是最高目标。用米沃什的话说,我们所面临的存在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在此’。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在此,而不在彼?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存在,感受自己的有效性,确认自己生命的意义,而不仅是像符号一样的活着。”
格非在多部小说里以知识分子为主角,但他们不再是兼济天下、以家国为己任的历史参与者,而是一个个边缘人,在急促的社会转型期无所适从。《春尽江南》里,诗人谭端午沦为无所事事的废人。《月落荒寺》中,宜生名利兼收,仍解决不了生命的空无。这些知识分子都不再是社会的主角,也无法通过劳动介入社会变革,他们要么迎合潮流,成为商业和政治的附庸,要么主动边缘化,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在格非的小说世界里,尤其是时间设定在上世纪90年代后的小说,知识分子要处理的不再是天下问题,而是地位落差后的矛盾。从《月落荒寺》联想到格非这20年的创作,他都在处理知识分子和商业社会的关系。格非意识到乡村的消亡不可避免,所以他写作《望春风》,弹奏一曲乡土的挽歌。同时,他看到知识分子在以都市为主的商业社会的无所适从,他写《春尽江南》,写《月落荒寺》,乃至更早的《欲望的旗帜》,都在探讨当知识分子不再崇高,甚至沦为“末人”,他们如何自处,又如何调节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格非并非仅仅为知识分子辩护和感伤,他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固有的局限,与其说这一代知识分子在边缘化,不如说他们离开了本就虚高的位置,20世纪为知识分子制造了幻梦,很快又捏碎,循环往复,直到心如死灰。
当格非回溯历史,他发现当今知识分子的困惑,早在历史上就多次浮现,比如他屡屡提及的《金瓶梅》和明中后期社会,那就是一个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士人集体困惑、堕落的时代。在格非看来,《金瓶梅》的问题既是明代的,也是现代的,他写了那么多小说,都在回应《金瓶梅》,因为那是他最喜爱的小说之一,他曾公开表示,自己对《金瓶梅》的推崇更甚于《红楼梦》。
但是,格非在完成“江南三部曲”后,他的创作也出现了某种瓶颈。一个是题材和人物关系的自我重复,一个是叙述语言的知识分子腔。格非写得最传神的人物是知识分子和充满欲望的女性,但在描绘其他人物时,就显得概念、空泛。《月落荒寺》里的楚云,在人物塑造上并不如宜生饱满,她更像一个知识分子想象的女性,投射梦幻和欲望的符号。自始至终,楚云更像知识分子的一个梦、一个情人,她不涉及柴米油盐,没有自己的脾气,她的出现和消失都是功能性的,为小说的情节服务。
《月落荒寺》中的女性大多是被动的、功能性的,缺乏自己内在的张力。比如第32节,楚云去接待一个来自美国的教育团,想起她当年在芝加哥,一个老外和她搭讪,随手搂住她的肩膀,小说写道:“刚到美国的楚云,觉得拒绝人家有点不太礼貌,就怯生生地答应了。那个人将她直接带回了自己的公寓。楚云糊里糊涂地跟他上了床。”楚云在这里完全是被动的,她为什么跟那人回家,为什么上床,她的心态变化是怎样的,在小说中没有交代。仿佛她就这么轻易地把自己交了出去。在完事后,楚云虽感到一点屈辱,但小说对此仅是一笔带过,旋即转入楚云和那人温和的对话。
同样,宜生妻子和加拿大男人之间,妻子也是一个被欲望牵引、模糊不清的符号,妻子具体的心境,在小说中也被隐而不表,我们能看到的,是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叙述,而女性只是充当配角、符号和欲望的化身。
格非写知识分子,更关心他们世俗的一面,精神的崇高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的欲望。当现实压垮理想,人被琐碎缠绕,主人公们产生厌世情绪,而稍微能救济他们的是书本和女人,但对这二者的依赖,也在无形中消磨他们。
在格非的小说中,知识和女性是两大叙事动力,也是欲望横生和毁灭的表层原因,女人成为格非小说中典型的喻体,女人越蓬勃,越反衬男性知识分子的空无,女人的介入和离开,成为知识分子在失势以后,对过往的追忆和对现世的嗟叹的触发机关。千禧年后,格非虽然退出了先锋姿态,用更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作,但他的思考仍是先锋的,延续着他在《欲望的旗帜》里的表达:知识分子被三重落差压得喘不过气——理想和现实、过去和现在、欲望和萎靡。
固然,格非对知识分子书写存在反思,早在《隐身衣》和“江南三部曲”里,他就不乏对知识分子自恋的讽刺,对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建构的历史保持怀疑,比如《隐身衣》中,一个做胆机的生意人对教授不吐不快:“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这段话,其实就是格非借人物说话,言说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
在阅读格非的小说时,我想到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在《荒原》中,艾略特借鱼王的遭遇描写了现代人精神的衰弱,当“上帝死了”,西方人面对的是一个道德沦丧、性爱泛滥,可人们又无法找到更高追求的荒凉境况。无独有偶,在那个迷惘的年代,乔伊斯、卡夫卡、伍尔夫等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涉足了现代人这种“荒原”处境,它是在崇高精神被瓦解后,知识人面对琐碎和物质过剩的年代的无所适从。
百年之后,当艾略特已离开人世,知识人的荒原处境却并非消解,反而在第三世界里如幽灵般回荡。中国知识分子在市场化大潮后经历的,实则是欧美诸国在20世纪城市化、商品化进程中的回音,但所不同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不仅仅是因为商品浪潮的冲刷,它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互联网年代技术革命,还有整个社会对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的信奉,都削弱了知识分子的地位。随之,知识分子不得不从其他角度接纳自己,在一个全新的浪潮中,寻找自己的合适坐标。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而格非的小说,若是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考量,就是对这个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荒原”现象的心灵写照。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