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青年作家郑小驴的小说,总能被那些投射在女性身上的情感所吸引。然而,研究界在关注郑小驴的历史叙事、乡村书写的写作之时,却鲜少关注他小说里的那些女性。笔者以为,郑小驴通过女性来书写人性之美,对女性的塑造集中表现了郑小驴对崇高精神的不懈追求。
一
郑小驴曾说自己写过很多灰色、阴冷、充满着失败主义的小说。也许,苦涩、孤独、迷茫的童年给他的小说染上了一层厌世的基调,他笔下的男性总是在直面现实的困境中进行痛苦且沮丧的挣扎。对于女性他却心存敬意、饱含深情,他笔下的女性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一切美好价值的象征。
《1986:春天的咒语》里那位腆着大肚子、从油菜花丛中走来的女人,一个人朝黑夜的深处走去,走过无边无际的荒原,蹚过水流湍急的清江,翻过荒无人烟的高山,穿过大片大片的梯田,才抵达生命的堤岸。后来,她以不同的身份在郑小驴的小说中反复重现。北妹就是一位。北妹在亲人面前能够吞吐一切委屈,但瘦弱的身躯并不娇弱。在随时都可被抓走的危险环境中,她依然是积极乐观的,夜晚教母亲和姐姐织毛衣,绣十字绣,聊着女人们亲密无间的闺中密语。即使她们并不认同丈夫与婆婆的生育观念,但还是默默接受了加诸给她的生育使命。在失去孩子以后,她终于无法承受一切而跳了河。她们勤劳、隐忍、勇敢,是作者对于至高人性的理想化表达。
那些女性身上散发着与生俱来的女性美。北妹“有一张洁白的瓜子脸,秀气而澄澈的眼睛,脸上带着瓷器般的光泽”。年轻的班主任李菲温柔可人,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香水味“霸道地侵入我敏感的嗅觉神经”。姐姐左兰是石门远近闻名的美人胚子。哑巴阿倾虽然是温泉度假区的小姐,但不施粉黛,也不染头发,浑身上下焕发出超脱的清秀清纯,“看上去像一位大学生”。在这里,作者有意把阿倾和其他人区分开来,读者能够感受到一种精神的牵引。这种牵引落实在小说里,就是游离对阿倾产生了好感,想要靠近她、追求她,在读者这里则变成了一种对美的获得与满足。
女性向往美好爱情,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但也需为此承受命运的悲剧。即使在命运不济的现实面前,她们也能够葆有为爱情牺牲的巨大勇气。女教师李菲勇敢地爱上青年音乐老师。左兰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沈老师,为此承受了巨大的伤痛,但她依然坚持要生下孩子、独立抚养,在被大方欺负失去孩子后,她并未因此妥协,依然与命运抗争,终于去到城里生活,走上一条她认为可以彻底摆脱女性悲剧命运的道路。无论是作为母亲那样的传统女性,还是外出打工、见过世面的北妹,有着服装设计师梦想的乡村女青年左兰,抑或是向往纯粹爱情的都市知识女性顾烨、张舸,她们承袭了东方女性身上的道德美、心灵美。同时,我们也能读到她们身上背负着很多固有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的重荷,在追求新的生活、新的自我实现过程中承载着时代之痛。
二
生活激活了创作,作家用语言的冒险来完成创作。2006年夏天,在炎热的长沙租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毕业、就业、到处碰壁,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在孤独、无奈与绝望的现实境况里,郑小驴找到了创作的秘密通道,打开了小说之门。郑小驴是这样记载写小说的那个夜晚的:“我那么激动,所有苦难、幻想、忧愁都被激活了。”郑小驴一次次以文学的方式重回“村庄”,写下了那些来自“村庄”的女性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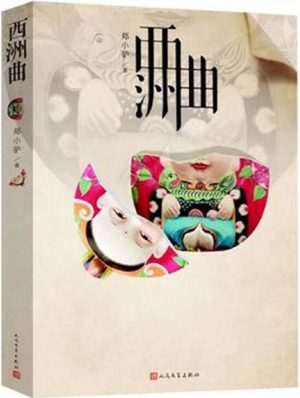
《西洲曲》,郑小驴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郑小驴并不正面讴歌女性,而是营造了一种充满悲情的叙述情绪。叙事的激情从审判开始。一方面,郑小驴在小说中以饱蘸情感的叙述书写女性对生命的守护。那个腆着大肚子的女人,在寒风肆意的夜里,挑着一盏马灯,在荒凉、崎岖、逼近死亡的绝境中艰难跋涉,勇敢地面对难产鬼、千年屋、超度亡魂的锣鼓声以及山岗上乌鸦“野性而凄惨的悲呼”而不退却。在这里作者首先自我定罪,出生就是苦的,叙述的基调就是苦的。另一方面又赞颂她们尝试打破固化的道德传统,不可逆转地、勇敢地走出村庄。不仅如此,郑小驴还注意把人物放置于生活的各种联系中,让历史进行评判。比如《西洲曲》写“我”替副镇长的独生子罗奎给女同学水芹送信,水芹收到信脸就红了,但就在那一天,“我”看到水芹“将肩膀的头发往后拨了一拨”,也看到“平日内向的水芹表现出了少有的活泼的一面,竟然还和几个好玩的女生玩起了追逐的游戏”。把水芹放置在几段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水芹的精神世界也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了。作者继续写下多年后再见到水芹的情景。她已经嫁给了大他一轮的电子厂的小头目,并且以见过世面的姿态在“我”面前展现了她的自信,这些女性,或忍气吞声,或独立自强,抑或随波逐流,她们都印刻着作者对崇高精神的孜孜追求。
在日常生活中深情讴歌女性之美。郑小驴擅长从平凡生活中吸取题材,写那些卑微的女性如何面对村巷旋涡、家庭与乡邻矛盾,着意于表现时代风云在普通女性灵魂的折光。他注重通过对人物言行举止的精雕细琢,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或是一句话,准确而微妙地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比如,左兰结婚多年后在街上碰到开美容美发店的小学同桌,同学问她服装设计师的梦是否已经实现,左兰只是邀请对方来自己开的小服装店逛逛。同学请她吃饭也被谢绝。最后,她对自己说,要送女儿朵朵去巴黎,成为一名顶尖级服装设计师,完成自己的梦想。一系列细致的刻画中,那个从未停下追逐梦想脚步的左兰在读者面前展开。
通过女性之间、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对比表现复杂的人性。长篇小说《西洲曲》在一个时空里并置了多组具有对比性的关系,北妹和丈夫谭青,母亲和父亲,罗镇长、八叔,姐姐和大方、李良,水芹、谭纬、罗奎和“我”,他们有着各自独特的性格命运,但在处理同一件事时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表现出了不同的姿态,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人物的悲与欢、忧与乐、堕落与上进对比中,构成了生命的曲线。所以我们读到,水芹用自己的行动一步一步地滑进时代命运的泥坑,左兰用她的抗争赢得了命运的主动权,进了城,开了店,可以自己决定生不生二胎。郑小驴还注意塑造那些被时代裹挟、席卷而迷失自我的女性,衬托少数女性的不懈抗争成果来之不易。
三
女性以卑贱柔弱的躯体承受无尽的苦难而变得崇高。对女性美的书写,体现了郑小驴对人性美孜孜不倦的追求。那些女性质朴、自然、毫无矫饰,隐忍、执着、勤劳,她们参与时代社会发展,书写着时代精神,代表社会前进的力量。女性在推动时代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作者内心的精神期待,体现了作家的创作理想。他期望在小说中抵达一个美的崇高境界,一种近似于诗歌和音乐那样震撼人心的艺术境界,正如作者写到的李菲和音乐教师合唱的情景,“那么崇高,值得尊敬”。精神的复杂性也正体现于此。
郑小驴在小说中,通过悲剧命运来表现崇高的女性美,尤其是那些天真无邪的未成年女性突如其来的悲剧命运。黎黎、果果清纯可爱,作为美的化身存在,她们又是悲剧命运的承载者。黎黎突然失踪了,护林员父亲从此踏上了漫长艰难而无果的寻亲之旅。他从林场找到海南,再找到城市里,都没有结果。放牛娃因为幼年的一些无知之举,从此背负着害死黎黎的罪名。天真的果果无意间说“被欺负”了,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导致了庆松的死以及父亲的悲剧。郑小驴试图通过她们身上的这种时代之痛,以及她们在无意间和那些命运达成和解、消融,成就崇高的永恒女性。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伟大女性的母亲在郑小驴的笔下却没有名字。或许,郑小驴在小说中写到的母亲,代表的只是那份源自人们心底的真爱。这种爱有如大地一般博大,如水一般温柔、纯净,她能够孕育出生命和理想。
也许,郑小驴的内心一直深埋着一位少女,没有具体所指,却作为精神原型存在着,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的力量,爱恨交织、悲喜交织,或毁灭,或重生,自我反思、自我解构、自我成长、自我救赎,历尽艰难沧桑和精神内省之后超脱出来,回到纯粹,回到美好,带着不可遏止的生机走向成熟。她们是“村庄”的精魂,演绎着她们自己的人生悲喜,呈现的是作者自身的精神迷惘与归去来。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