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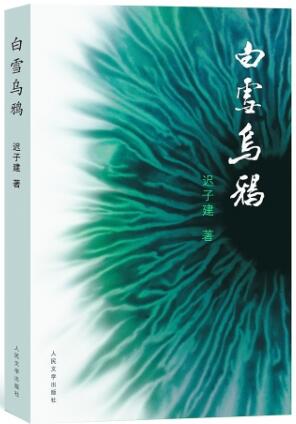
《白雪乌鸦》,迟子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这个春天无疑是特殊的,新冠疫情的突如其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种波澜当然会传递到文学的世界之中。一段时间以来,“文学介入”“作家如何书写灾难”等话题引起了文学界的热烈讨论,那些成功处理过瘟疫灾难题材的经典文学作品,也被频繁地提起和重温——加缪的《鼠疫》、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当然,这一串名单内也不会缺少中国作家近年来的创作成果,例如迟子建的《白雪乌鸦》。
清朝末年,一场严重的鼠疫灾难笼罩了东北,生活在哈尔滨傅家甸的人们,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被集体推到了生与死的角力边界上——这便是长篇小说《白雪乌鸦》讲述的故事。从题材分类上来说,这个故事可以被归入“重大历史题材”:它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迟子建在本书后记中,专门讲到自己疯狂查阅和“吞吃”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历史材料的情况),而“瘟疫”,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又总是反复出现、影响巨大,因而是极富重要性和代表性的。这样的基本定位,使《白雪乌鸦》在最直观、最总体的意义上显示出沉甸甸的分量——我们能够将这个故事与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着的苦难对照阅读,并且它会在人类历史记忆的长河中激起幽深的回声。
瘟疫与历史
瘟疫,连同它所带来的大规模死亡及社会危机事件,无疑是古老的,甚至带有某种经典性的人类经验;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对“瘟疫”两个字感到陌生。许多重大的历史进程背后,都有着瘟疫力量的影子。雅典的衰落,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袭击雅典的严重瘟疫有重大关系,而雅典这一海洋贸易秩序主导者的衰落,又加速了地中海文化圈的整体格局演变。与此类似的,是曾经发生在美洲“新大陆”上的事情:相比于铁器、马匹和火枪,病毒对规模巨大,但缺少相应免疫力的美洲大陆原住民来说,才是更加毁灭性的因素。若非病毒,西方文明对美洲大陆的介入和改造,或许将在另一种缓慢、艰难、渐进、温和的节奏中完成。
瘟疫的传播本身,与世界各地区之间愈加频繁的贸易往来关系密切,同时瘟疫对权力格局的重塑,也反过来刺激着历史的开放性姿态的形成(如黑死病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冲击,间接地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由此可见,无论在古典时期的人类文明交流,还是近现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之中,瘟疫,常常潜伏在表层历史叙事的背后,发挥着自己隐秘的力量。甚至,它本身便是人类文明集中发展的产物和象征——正如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当人口的数量和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也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至少能够形成并保持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的人群病。”人口的聚集、资源的交换、文明的演进,同瘟疫的滋生之间,其实存在着同构伴生的关系。
“事故”与“故事”
因此,我们不能将瘟疫仅仅视为孤立、偶发的自然事件。相反,在瘟疫的身上,寄寓着鲜明的社会性象征:它寄生在人类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之上,并对复杂关系中的人类群体(及其在集体性灾难事件中的应激反应)投去锐利深远的凝视。
我想,也正是由于此种缘故,瘟疫才得以为文学书写提供独特的视角与契机,从而一再地受到作家的青睐:那种集体性、突发性的极端处境,使得长期淹没在浩瀚人群中的矛盾张力及自我思考,以一种既富戏剧性又具合法性的方式集中爆发呈现出来。并且从技术层面看,瘟疫的语境,能够满足文学叙事中某些特殊的功能需求,而又不至因过于突兀而引发读者的“排异反应”。正如青年评论家刘诗宇近日在《讲故事的人,与这面现实和人性的镜子——论叙事与“疫病”》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当作者需要同时调动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就需要在叙事上安排能够聚集大多数人物的群体性事件,而一旦作者产生了‘极端’的要求——例如需要大量的角色‘消失’,需要大多数角色在短时间呈现出与常态相反的性格时,就只有战争、瘟疫等‘重头戏’方能生效。”
这种极端性的“聚集”和“反常”,正是《白雪乌鸦》这部小说的出发之处。小说开篇的情景,便是王春申在1910年的深秋夜晚,赶着马车回到了傅家甸。这样一个“到来”模式的开头,本身便是“聚集”的微观象征(个体“到来”是群体“聚集”的分子化描述)。而王春申这一人物的职业,又恰恰是拉车——于是,随着王春申的脚步与视野,越来越多的人物被聚拢进故事,随之聚拢而来的还有关联着各色人物的各条故事线索。所有这些人物,因鼠疫封城而被高密度地聚拢在傅家甸这片小小的空间;进而,千丝万缕的人物关系线索,也由于人物角色的高密度聚集和突发性“反常事件”冲撞,而将平日里暗藏潜隐的纠缠形态完全袒露了出来。
在此意义上,《白雪乌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群像式的书写。它让我们想起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那个故事里,交通管制使得公共电车这一密闭空间内的各色人物之间,发生了短暂(却不失亲密)的关联。然而,与《封锁》不同的是,《白雪乌鸦》的故事,发生在古老、真实、稳定的文化语境之中——傅家甸,其实是分享着都市外壳的“乡土中国”,尽管它是哈尔滨(现代城市)的一部分,实际上却保留着自身独特的文化气息、话语谱系及情感模式,更像是人情味浓厚的“熟人社会”,而非探险家和流浪汉钟情的“陌生人社会”。这样一块镶嵌在现代都市文明与传统乡土文明之间的小小飞地,能够将“事故”(反常经验)归化为“故事”(日常经验的特殊形态)。
“反常”与“恒常”
傅家甸,这片瘟疫笼罩下的小小的“生死场”,因此在生与死、重压与萌发之间,绽放出巨大的情感张力。如同“传染”的另类隐喻,那么多的命运轨迹发生了交集,随之交叠的是一张张表情生动的脸。善良隐忍的翟芳桂、命途多舛的王春申、活泼喜人的喜岁、贤惠聪颖的于晴秀……一系列具有独立性的人物形象,在突发灾难的冲击淘洗中渐渐碰撞、重影、合一,那苦难与温情混融折射后映出的光彩,恰如生活自身的色调。相类似的,傅百川荣耀背后的难言苦楚,翟役生恶行背后的辛酸创痛,也都暗示着表层生活图景背后心灵和记忆的复杂景深。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从“反常”恐惧里慢慢觉醒的“恒常”力量,看到了生死绝境里愈加清楚鲜明的人间况味。就像小说题目里的“乌鸦”,这黑色的、不祥的死亡力量象征,却在迟子建的笔下变得亲近:“翟芳桂不讨厌乌鸦……它那粗哑的叫声,带着满腔的幽怨,有人间的色彩。”甚至当疫情散去,乌鸦还用它的血肉发挥了催奶的功效——滋养着满怀希望来到这世界的新人们。
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王春申的眼睛湿了,因为他从这些坏掉的时间中,看见了谢尼科娃青春的脸。”在无人钟表店里悄然落泪的王春申深深地打动了我,并且完美地收束了这个故事。说到底,迟子建最为关注的,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有血有肉的人;而瘟疫,及其所带来的聚集与反常,恰到好处地为日常生活及人类内心世界的诗意铺展,搭建了一方汇拢目光的舞台。灾难凶猛,生死无情,种种的秩序乃至常识都面临颠覆。但人心始终柔软,生活万古常青,动荡之中亦有慰藉与平和。在生死反常、人间失序的语境里,那些最寻常的、平日在浩荡的人类生活经验洪流中被轻易稀释的情感与品质,发出了格外耀眼的光辉。
而这,正是我们在形形色色的灾难题材文学创作之中,最渴望看到的东西。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