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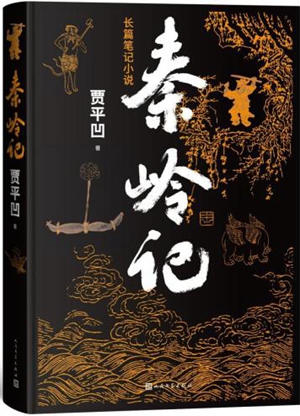
《秦岭记》,贾平凹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老实憨厚的跛子因为一场意外事故换肾后脾气性格、为人处事方式一下子判若两人,从过去令人同情、招人怜爱变得人见人怕、招人讨厌,村里人怀疑此乃皆因换肾所致;三位盗挖盗卖被村民视为保护神的古银杏树偷盗者,初盗者因偷挖时被狗咬伤死于狂犬病、转卖者妻子殁于倒卖古树途中拖拉机翻车事故、窝藏者父亲因儿子被公安局抓走心脏病猝发而死;飞猪寨养猪专业户孙全本的猪不仅能听懂夫妻俩对话,还能看见两个门神从门扇上走下来打架;二郎山的獾长一副人脸,还敢当猎人面笑着往火堆里撒尿……神奇灵异的故事频频呈现,一座山环水绕、云雾升腾、万物繁荣地矗立在人界与灵界之间的苍茫山岭神秘纷杂的精神世界,随即在作者本真自适、从容不迫地讲述中一一呈现,并以一种缥缈而又现实、玄幻而又真实可感的灵性光芒,弥补、拓展、丰富了我对一座非凡山岭已有的理解与认知。
这是我阅读贾平凹新作《秦岭记》时的直觉感受。
从幕后走到前台
秦岭是中国大陆三条东西走向山脉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对中国大陆地质地理构成和自然生态格局形成、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国传统文化诞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影响。贾平凹老家商洛处于东西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山脉中段腹地,群山绵延、谷岭纵横、山水交错、丛林莽莽、万物繁荣,是秦岭自然山水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以秦头楚尾为标志的南北方文化交汇交融地带和楚文化发源地。这里地理独特、山水奇异、风俗迥异、文化古老,一直是贾平凹文学地理根脉所系。从早年的《浮躁》和《商州》系列,到后来的《秦腔》《古炉》《高兴》《带灯》,再到《老生》《山本》,我们发现秦岭之于贾平凹正如马孔多镇之于马尔克斯、奥克斯富镇之于福克纳一样,既是他的文学故乡和创作原发地,也是作者的精神原乡。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以秦岭为背景的多元化书写,不仅让秦岭成为贾平凹面向现实、历史与生命本体多重叙事的在场者和推动者,贾平凹对秦岭自然山水、文化精神近乎迷醉地持续书写,也让莽莽秦岭成为贾平凹作为当代中国极具中国文化意识和文化立场,具有独立的文学品性、精神思考和独特地理与地域文化标识作家的塑造者。
然而,相对于此前将秦岭作为映现作者笔下纷繁故事的发生地和贾平凹式生活叙事的背景而言,以秦岭自然山水和生活其间的草木鸟兽、自然天籁、生灵万物、芸芸众生为书写对象的《秦岭记》,则是一部淋漓着秦岭本体文化意识和生命气象的秦岭精神之书、灵魂之书。在这部被学界定义为“笔记体小说”的作品里,遍地峻岭古木、终年云雾缭绕的秦岭已不是过去作者结构情节的背景,也不是演绎故事、推进生活叙事的场景和道具,与秦岭本体徒手相见,坦然面对,见山见水的面对面书写,让秦岭前所未有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由配角变为主角,成为结构这部看似散漫率性、魔幻空灵,实则充满淋漓尽致的现实质感的奇异文体的主体和作者主体意识的开掘者、生发者和表述者。而在贾平凹此前与秦岭相关的众多作品中,秦岭及其自然山水仅是作者有意设置的特定环境下故事的发生地、地理与文化意义上地域性标识,与作品主体意义和作者主体意识关联度并不直接。即便是在动笔写作之前作者最初准备取名《秦岭志》的《山本》里,秦岭依然是那个纷乱年代特定环境下诸多残忍与凄美故事的见证者,秦岭本身并非《山本》故事的演绎者和创造者。也就是说在《秦岭记》之前,在贾平凹持续不断的秦岭书写里,秦岭始终是作者由于叙事和结构需要而特意设置的环境文本而非主体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完全可以独立于作品本体之外,作者言说的主体也不是秦岭本身。但《秦岭记》的出现,无论对于贾平凹和秦岭,还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坛都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对于贾平凹而言,《秦岭记》不仅开创了他几乎持续一生的“秦岭书写”的新境界,也标志着贾平凹对一座寄予了他终生文化与精神情感的山岭——秦岭的认知与写作,已经从对自然意义上的秦岭局部关注进入到对秦岭自然万物的整体书写、从秦岭自然山川的外部描写深入到了对秦岭文化精神的理性呈现;作者与秦岭的关系也从过去的互相观望、各自独立一跃而为物我相融、互为依存、血肉相融,互为各自灵魂与精神世界的言说者和表达者。在《秦岭记》里,已经与作者精神和意识融为一体的秦岭是《秦岭记》唯一的主角,也是《秦岭记》众多充满魔幻色彩的灵异故事和蕴含了现实人生真味的人间故事的唯一呈现者和讲述者。对于当下文坛来说,无论从文体结构还是文本开掘上,《秦岭记》超越传统意义上小说与散文文本、自由而灵动的跨文体写作以及由物及人,以一座自然山岭为书写对象的主体意识,都开拓了中国当代叙述体文学写作新天地。因为在《秦岭记》之前,当代中国文坛还鲜有以一座自然山岭本体为书写对象,且在文体结构上如此率性自由、从容不迫,既不拘泥于传统小说或散文讲求故事和结构的整体性,又突破了主题与线索互为表里的作品。尤其是为了凸显《秦岭记》主旨,作者有意为之的梦境与人境杂合、幻境与现实交错,物界与人界相互沟通、彼此映照的灵性写作,不仅让作者的主体意识得以淋漓尽致地表达,也让作者刻意塑造的他所理解的精神与文化意义上的秦岭形象在形而上和形而下同时得以确立。在《山本》里,贾平凹说秦岭是“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而到了《秦岭记》,已经被他反反复复书写了一生的秦岭,俨然已被作者的主体意识和精神情感唤醒、复活并活生生站立起来,成为一个血肉饱满、伟岸磅礴、灵光四射、精神与情感毕现的生命体:“它太顶天立地,势力四方,混沌,磅礴,伟大丰富了,不可理解,没人能够把握。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秦岭记·后记》)”贾平凹这种对秦岭精神与文化意义上的理解与认知,不仅让一座自然山岭回归于人文与生命本体,也让秦岭成为一座有血肉、有灵魂、有思想,也有喜怒哀乐的人间情感的非凡山岭。
《秦岭记》为我们展示并塑造的秦岭,既是亘古以来就附着在秦岭山山水水的万千生命的演绎者和庇护者,也是以秦岭为中心的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维护者。而具体到作家的主体意识,《秦岭记》则借助于发生在秦岭山区的山水树木、花鸟虫兽、寥落人间、生灵万物之间的种种或灵异神奇,或真实有据的故事,实现了作者基于一座自然山岭的启发、启示所获得的对生命本体、世事沧桑、人间百态,以及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相因关系、生命哲学、文化精神的思考与表达。
中国文化与秦岭文化的建构
板桥湾有个风俗:新盖的房子须得先让狗进去占吉凶。经历了公社化饥不择食的困难时期,板桥村的狗被宰杀殆尽,和光棍柯文龙朝夕相伴的狗便成为全村硕果仅存的“测屋者”。柯文龙的狗不仅善测新房吉凶,还能听懂人话、知晓人事、分辨飞禽走兽气味、叫出花草树木名字、看见人眼看不见的东西。因此,柯文龙与狗亲密无间,形影不离:“出门去干活开会赶集,他是狗的主子、领导、首脑,他保护着狗,回到家里,狗又是他的答应、保姆、常在,狗侍候着他。想吃烟了,他说:我烟袋呢?狗会爬上柜台在一个木盘里把烟袋叼来。他说:天要黑了,鸡该进笼了。狗就到屋前的场子上赶鸡,鸡不听它的话,鸡犬吵闹一番,鸡最后还是进了笼。六月里在地里锄苞谷苗,被白雨淋了,发起烧昏睡在炕上,狗是过一会儿就跑来,前爪子搭在炕沿上看他,每次看他睁开眼了,他说:没事。它才再卧到门口去。”1970年,大锅饭里已经舀不出一勺粥度过这个春天了,生产队长决定冒违法判罪风险,把集体耕地分给各家各户种。生产队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分地那天晚上,柯文龙开会时也把狗带去了。会议结束,队长发现拴在屋外的狗后抬腿就是一脚。回家后,挨了队长一脚的狗病了,三天后不见了踪影,柯文龙大病了一场。四年后,全国实行土地承包责任,队长才告诉柯文龙狗是他打死的,原因是狗偷听了秘密会议,怕他这只能听懂人话的狗把分地秘密透漏出去。队长还告诉柯文龙,他和另外三位村民把狗偷走打死后埋在了打麦场的皂角树下。柯文龙一听伤心至极,抱住皂角树就是一场痛哭。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柯文龙哭声一起,青天白日,皂角树每片叶子竟哗哗啦啦往下滴水,水滴了一地,“树底下的地上都能照出人影了”。另一个故事说,做人口普查的东阳县统计局干部白又文进驻秦岭南坡关山垴的葫芦村后,神经衰弱症又犯了。一个下玄月的晚上,白又文睡不着,便坐在村长家二楼看月亮。朦胧月色下,山林万物似乎都被隐约传来的石涧水声唤醒,蠢蠢欲动、生机勃勃。溟溟濛濛中,白又文不仅看见了散落在丛林中的人户鸡上架、猪入圈、犬息声、人入梦的死寂人间,还看到了白天躲避人户的百兽从树林里、山洞岩穴里走出来,潜伏在草丛里的蛐蛐、蚯蚓、湿湿虫也争先恐跑了出来。正在白又文感叹原来黑夜里并不是万物安息的时候,更加令他惊异的一幕出现了:他看见全村男女老少从林子里出来,聚拢在村前的沟壑上,平日里怪石嶙峋的沟壑变成一片平平坦坦的草甸。回头再看,他看见梁三和伤疤脸边解板边吵架;村子照壁下几个老汉边吃旱烟边聊天、东坡上坐的三只母麝在叉开腿招惹蚊虫、刘三踅担粪路上和路上的一条鱼说话、张保卫边打胡基边放响屁、村长在训二栓子、巷道里老童又在打老婆、路过的张三说老童之所以经常打老婆是因为老童前世是老婆娘家的一头驴……再后来,白又文开始夜游。他走下楼台、走进人群,一只鹅喊他的名字、一头猪前脚搭在圈墙上哼哼唧唧朝他笑、一位白发老太太在菜地里捡人民币、会计吆喝村民到西山梁上采五味子……白又文就这样在似幻非幻、似睡非睡,现实与幻界交错中度过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和村长聊起才发现,自己昨晚闯入了村长的梦境,他看见了村长的梦、也看见了全村人的梦,于是感叹说:“梦是现实世界外的另一个世界,人活一辈子其实是活了两辈子。”从此以后,白又文再也无法把现实生活和梦境所见分辨开了。不仅如此,能像人一样直立行走还会说人话的金丝猴、活着时能看见鬼魂世界死后肉身变成一截石头的老和尚、有喜怒哀乐的花草树木、和鱼店老板对话的鱼等,充满魔幻色彩的灵异事件和超自然现象频频出现于《秦岭记》所讲述的各色各样故事之中,而且众多寄居于秦岭高山丛林、原本与人间分属两界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在被作者赋予灵性、神性和人性后,成为结构故事、演化情节、强化《秦岭记》主体意识的主角与原动力。于是,一座非凡山岭万物共生、人界与灵界并存、幻境与现实互照,生机勃勃,弥漫着神秘智慧精神灵光的灵魂与魂魄,在作者率性而富于诗情和诗意的讲述中徐徐呈现。
对于贾平凹文学作品频频出现的灵异现象,有人归结于神秘主义叙事,也有认为贾平凹秉承了《山海经》和《聊斋志异》笔记体志怪小说传统。但在我看来,贾平凹是一位真正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致和特殊偏好的作家。笼罩在贾平凹与秦岭相关作品中的那种佛道相融、巫觋盛行、人鬼并存、万物有灵的神秘气氛,源于作者与生俱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沉迷与体认,也源于秦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源地所培植的深得儒、释、道文化精髓的秦岭文化的滋养与影响。秦岭文化是中国内陆东西文化、南北文化的综合体,也是孕育并催生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文化。作为中华祖脉、华夏龙脉和中华民族父亲山,自青藏高原东缘昆仑山断层蜿蜒向东,一直延伸至淮河之滨的秦岭山脉,地处中国大陆版图中央,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萌芽、发生、发展、成熟、壮大的核心腹地,秦风楚韵、巴蜀风情交相辉映,秦文化、楚文化、关陇文化、中原文化、羌藏文化、兵戎文化、移民文化、宗族文化积淀融合、相互渗透。时至今日,东西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山区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万物有灵,重祀好巫,相信来世,倾心灵魂关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自然崇拜、天地崇拜、先祖崇拜为特征的古老文化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地存活在秦岭山区,至今仍是人们对待天道人事、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规范日常行为的精神准则。贾平凹老家商洛地处秦岭腹地、丹江上游,又是以尚鬼、好巫、重祀为特征的楚文化发源地,从小耳濡目染,古老神秘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自然而然,不仅成为他审视世界、参悟人生、认知生命的文化语境,也成为贯穿他文学创作始终的精神意象。因此,就弥漫于贾平凹作品的神秘主义文化特质而言,其实与《山海经》和《聊斋志异》并无多大关系。真正让贾平凹对精灵鬼怪、神巫仙道、灵异生命等超自然现象沉迷的根本,乃是秦岭山区和老家商洛特有的地域文化传统所赋予他的与生俱来、根深蒂固,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中国本土哲学并行不悖的本体文化意识。贾平凹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饶有兴致地探究种种神秘灵异现象与社会历史、现实人生、人类灵魂世界之间隐秘关系的写作,实际上是一位对中国本土文化精神充满兴致的作家的精神还乡,这也构成了贾平凹作为一位最具中国本土文化意识与中国传统人文情怀的作家独具一格的思维方式与美学追求。
荣格认为,中国人对宇宙万物带有神秘色彩的特殊感悟和思维方式。在贾平凹以往与秦岭有关的作品中,类似人是狼,狼也是人(《怀念狼》),以及可以在灵魂出窍后依附于动物身上俯瞰芸芸众生的癫痫病患者(《秦腔》)之类的书写,正好遵从了荣格所谓的中国人看待宇宙万物特有的思维方式。在《秦岭记》中,这种闪烁着灵异光彩、充斥着超自然的灵性叙事更是随处可见:可以轮回转世的猫、有灵魂的稻草人、有思想的桦树、与槐树有仇的啄木鸟等等,秦岭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生灵万物,都被作者赋予超现实的灵性与神性。这种带有浓厚神秘、灵异、魔幻色彩的叙事方式,一方面唤醒并呈现的是一座自然山岭内在的生命气象和精神脉动,另一方面则是作者借助自然万物表达自己对人类世界、生命本体认知的自主表达方式。任秋针不明原因的离奇死亡,揭示的是生死无常的生命真相;洪同中从梁双泉四个伯父、四个婶娘的生死,悟到的是一个人生有时死有地的道理,并慨叹说“其实人是一股气从地里冒出来的,从哪儿冒出来最后又从哪儿回去”;禳治会叫“奶奶”妖猫的道士对豆在田儿子养的那只连打五次都打不死的跛脚猫前世今生的解释,既包含了凡生命都是平等的和万物有灵的生命观,也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共同强调的因果观,以及秦王山上两棵桦树深信砍伐者手中桦木作柄的斧子不会砍伐它的同类,最终还是被砍伐所揭示的同类之间的互相残杀等等,诸如此类人界与灵界并行、魔界和现实共存、灵性抒写与灵魂拷问同步、哲学思考与生命真相揭秘互为映证的书写,不仅让《秦岭记》字里行间弥漫着超现实、超自然的灵性之光,多维度、多视觉、多层面完成了一座自然山岭的文化建构,也实现了作者基于中国文化传统角度对他体认的世界、生命、社会、人生、精神、灵魂本体哲学意义上的智性抒写与表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秦岭记》既是贾平凹献给一座他从精神和灵魂上顶礼膜拜的非凡山岭的真情之书,也是承载了贾平凹对现实人生和自然万物整体认知的灵魂之书。
灵异与魔幻后面的真相
初读《秦岭记》,面对贾平凹笔下灵界、幻界、魔界与人界相互交杂,梦幻人生和魔境幻象交错纷呈,现实人间与自然万象灵魂相映的抒写,我们不得不承认《秦岭记》是一个充满灵异魔幻精神存在的奇异文本。然而,一旦拨开笼罩在作品中缥缈升腾的玄幻迷雾我们会发现,《秦岭记》中的秦岭,正是那座在自然地理上真真切切矗立在中国南方与北方切割线上的中华龙脉秦岭;《秦岭记》中那些充满灵性的山水自然、花鸟虫兽,正是秦岭以它博大襟怀养育的生灵万物;《秦岭记》所演绎的世事沧桑,正是那些世世代代与秦岭相依为命的众生已经经历和还在经历的真实人间。只不过为了便于表达对一座伟大山岭及其生存其间的生灵万物生命本体的理解与认知,作者采用了一种既便于想象与抒情,又便于直抒胸臆地表达作者主体意识的灵性抒写方式,让遍布秦岭深处的花草山石、生灵万物都成为作品的主角和自主言说者、表达者。在基于对秦岭古老沉智文化传统和丰富博大生命本体精神层面高度认同前提下,《秦岭记》极具灵性与神性意味的抒写,以及《秦岭记》中众多看似神奇灵异、荒诞玄幻的离奇故事,云蒸霞蔚、扑朔迷离的超自然异象,不仅没有虚化真正意义上的秦岭文化精神和以秦岭为背景的当代生活现实景象,反而让一座有形体、有魂魄、有精神、也有灵魂,有跌宕起伏的历史身世,也有潮起潮落、风云变幻的现实遭际的山岭,显得更加伟岸高大、气血淋漓、真实可感。这正如马尔克斯所言“我相信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你可以写得轻松自如,思如泉涌”一样,弥漫于《秦岭记》的魔幻、神秘、灵异的精神光芒,既是作者刻意营造的便于表达的“特殊的精神状态”和秦岭文化原始状态,也是作者有意为之的言说方式。如果对真正的秦岭有所了解,我们就可以按图索骥,从《秦岭记》里读出一个生动鲜活、丰富多彩、精气神俱佳、万物繁盛、生命繁荣的秦岭。因此在我看来,这部貌似作者随心所欲、从容为之,内容涵盖秦岭天文地理、自然生态、历史宗教、文化精神、生命形态、山川万物的《秦岭记》,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秦岭志”,一部具有社会、人文、历史和精神认知价值的秦岭之书。
《秦岭记》中的灵异文化,源自秦岭文化本体。秦岭不仅是中国大陆最古老的山脉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缔造者。早在西周时期,地处秦岭中段的终南山就是中国古代原始宗教修行者云集的家园。老子在秦岭东部余脉函谷关写下后来成为道教宗教经典的《道德经五千言》并在楼观台设坛讲经后,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万物有灵、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精神,便在西起太白山,东到华山的八百里终南仙境扎根发芽,并经由秦岭传播到整个中华大地。后来,伴随着西域佛教落脚秦岭、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秦岭诞生、诞生于齐鲁的儒家学说在秦岭怀抱的西汉都城长安走上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文化舞台,以终南山为中心的秦岭成为儒释道及众多形形色色中国传统宗教共同争抢的舞台。到了盛唐,与大唐都城长安遥遥相望的终南山密林深处仙道往来、隐修者云集,佛教寺院、道教宫观鳞次栉比,一度形成“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为僧”这蔚为壮观的宗教盛景,并催生了在西方人看来最为神秘的中国文化景观——隐士文化。时至今日,古老的自然崇拜、天人合一、万物有灵、万物一体、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生死无常、祸福相依等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留存在秦岭南北日常生活细节之中。《秦岭记》中诸如竺岳上修成金刚不坏之身的和尚;打了几十年猎的猎人王卯生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意外事故后不仅收拾起刀枪不再当猎人,还悟出了“爱恨存于无常,生与死只在呼吸间”,“万物都浮沉于生长之门”,人没有理由随意残杀的人生哲理和生命哲学;跌了一跤昏醒之后能看见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预知还没有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的“神汉”王西来,以及豆在田儿子那只经道士禳治后因羞辱以头撞击石碑而死的跛脚猫等等,《秦岭记》频频出现的种种灵异现象和超自然神秘力量,以及由此生发的关于人间与自然类似寓言和箴言的哲思与独白,正是秦岭文化本体的形象化表白。
《秦岭记》呈现的自然状态的秦岭,正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秦岭。尽管从自然地理和生活相貌看,《秦岭记》里所展现的秦岭仅是以作者故乡商洛及终南山、太白山为中心的狭义上的秦岭,但作品用大量笔墨对秦岭山水形势、物产气候,以及金丝猴、羚牛、银杏、独叶草、水晶兰等动植物的诗意化的书写,已经足以涵盖东西绵延1600多公里的秦岭自然地理、人文精神和历史与现实。史重阳以毕生之精力上山采药、伏案写作《秦岭草药谱》,既塑造了一位沉醉于中国传统医学的太白山草医形象,也反映了秦岭作为“中国药山”丰富多样的中草药现状。草花山顶上两个山泉相距几十丈,却一个泉的水往南流下山,入了长江流域,一个泉的水往北流下山,入了黄河流域,讲的是秦岭是长江黄河分水岭。还有秦岭温泉、遍布丛林深处的清贫寂静的山间寺院、纵横交织的谷峪古道、山货聚集的山间小镇等等,都一如我十多年来一次又一次在秦岭深处往来穿行时所经历过的情形一样,神形俱备、韵味十足。如果用心琢磨,我们还可以将《秦岭记》中很多虚构的地名和现实中秦岭的许多地方相印证。比如作者说白乌山是一块整石形成,而地质学早已证明华山就是一整块花岗岩组成;竺岳上的“净水雉”,正是太白山大爷海一带经常出现的净水鸟;青云峡的神秘洞窟,对应的是商洛丹江两岸的“老人洞”(又称“神仙洞”);山顶有海子且终年积雪的白鹤山,就是太白山;民国时因县长被土匪所杀废弃的老城,正是周至老县城等等,只要用心揣摩,很多在《秦岭记》里被作者虚化或诗意化的山川地理、自然物产、历史人文,都可以与现实中的秦岭一一印证。
应该是作者刻意为之的灵性写作,让《秦岭记》笼罩着一种神奇灵异的神秘灵光,但只要细心阅读就会发现,《秦岭记》中许多故事和事件皆有来源和出处。如果将其中众多或离奇怪异或鲜活生动的故事联结起来,完全可以将《秦岭记》当作一部秦岭地区数十乃至上百年变迁史和全景式社会风俗图来解读。比如豆在田说他打猎时发现了老虎的故事原型,应该就是当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周老虎事件”;上元坝一夜之间崛起的别墅群白城子由盛而衰掀起的轩然大波,当为至今影响犹在的“秦岭事件”无疑;蝎子镇的兴衰映现的,是国家为保护秦岭环境而开展的小煤窑整治;秦岭南端漫峪里和茶盐古道豆沙垭风俗不同,语言各异的外地移民,反映的是明清以来“湖广填陕南”的秦岭移民史。此外,通过《秦岭记》中各色人等不同时期经历的诸如秦岭匪事、民国战乱、农业学大寨、水灾饥荒、包产到户、林权改革、移民搬迁、生态恶化、城市崛起、乡村凋敝等社会与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真切而具体地触摸到一座苍茫山岭所经历的世事沧桑和时代风云。而在文化层面,我们不仅能从《秦岭记》具有浓郁表现主义倾向的书写中明确无误地感受到儒释道共居一山、各种原始宗教与复杂多样的民间信仰相互交错的秦岭文化精神的历史与现状,还能从诸如作者对陕南孝歌、婚嫁葬俗、饮食建筑、日常习俗情趣盎然的描述中,获得一座具有特殊文化精神的山岭多姿多彩的文化与生活信息。尤其让我们不能将《秦岭记》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志怪小说”来看待的,是《秦岭记》看似散漫灵异的叙述中所映现的当代社会变革所引发的秦岭山区社会心态与人的精神情感的浮沉变迁:在几近荒废的喂子坪买古银杏树的蓝老板,在经历了令他毛骨悚然的灵异事件后一无所获,空手回到城里时突然发现城里的高楼,是秦岭里的山;街上跑的汽车,是秦岭山里跑出的野兽变的;而城里来往穿梭的茫茫人群,则“三分之一是人,三分之一是非人,三分之一是人还是非人,全穿得严实看不明白。”飞猪寨养猪专户孙大圣由野猪和家猪杂交养猪改用催肥剂养猪后,吃了添加剂的猪长得飞快,望像嫦娥一样飞到天上的离奇故事,反映的是市场经济对山里人精神世界的侵袭与污染。西后岔女性一茬一茬外流,原本美女成群的西后岔男人也因娶不上老婆纷纷外出打工或逃往他乡,留下的白痴和残疾人“人吃啥狗吃啥,牛干啥他干啥,丧失了尊严,没有了羞耻,连脸也不洗”的描述,是当今偏远乡村走向凋敝、衰败、衰落的真实写照。独堆山因一棵有六百年树龄的桂树重新修庙塑像,很快形成一座游客如织的旅游小镇。然而,守着寺庙挣钱的山里人却每天白天把鱼鳖卖给香客,晚上又把香客放入老桂树下放生池放生的鱼鳖捞回来第二天再卖的故事,是市场经济冲击下唯利是图、金钱利益至上取代诚实纯朴,人心不古、信仰缺失的社会现实。一场雷电引发的大火将庙宇化为灰烬,小镇生活重归以往,既是作者有意设置的富于宿命色彩的结局,也包含了作者对当下社会善恶良知、道德失衡的悲悯与批判。“而桂树还在,树上的金黄花蕊在这一夜里全部堕落,地上铺了一层,足有四指厚”的抒写,则既是献给市场经济雾霭愈来愈沉重地蒙蔽并湮没人的精神世界的时代悼歌,也是对现代文明冲击下渐行渐远的中国朴素乡土精神情感的深切哀叹。至于魔术师鱼化腾在向大家揭示魔术背后的秘密时所发出的“真相是永远没有真相啊”的感叹、小时候脑袋被驴踢后看什么都非黑即白的胡会众、由于一个梦不再做油炸肉芽生意的老信、因一块意外所得的巨大水晶石反目为仇的张姓兄弟,以及戴帽山119岁老人和村长极具哲理的对话、能听见树上的花开口说话而且断定许多谎花是树在说谎话的苟门扇、两个村支书和村长模样争吵不休的有灵魂的稻草人等等看似魔幻离奇的讲述,无不都是作者对当下社会心态、现实人心单刀直入地迫视、揭示、解析与批判。
总之,从文本意义上来说,《秦岭记》既是一部以根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本体的灵性抒写,全方位阐释一座非凡山岭文化精神的激情之书,也是一部凝聚了作者基于大变革的时代语境下对当下中国社会心理、世道良心、人心人性、文化精神、情感意识起落浮沉、漂浮不安现实境况的真实感受与把握,对自然万物、生命本体、人类灵魂相互关系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与认知的智性之书。唯有如此,面对《秦岭记》里种种神奇诡秘的灵异现象和既真切实在又虚幻缥缈的现实人生,我们才能理解作者《秦岭记》后记中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写秦岭。写它历史的光荣和苦难,写它现实的振兴和忧患,写它山水草木和飞禽走兽的形胜,写它儒释道加红色革命的精神。先还是着眼于秦岭里的商州,后是放大到整个秦岭。如果概括一句话,那就是:秦岭和秦岭里的我。”正是基于作者“秦岭和秦岭里的我”写作意旨,我们还可以确认《秦岭记》里其实有两个主角:一个是生生不息、孕育万物、包容万物的秦岭,一个则是借助一座苍茫山岭完成自我表达的作者本人。尽管它们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一个属于自然范畴、一个身处现实人间,但由于作者富于精神意味的抒写言说,弥漫在《秦岭记》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有灵、万物相容的文化精神,以及作者渴望“把自己写成了秦岭里的一棵小树”的创作意识,不仅让自始至终都并行不悖穿行于《秦岭记》始末的两个主角物我相容、合二为一,成为难分彼此的整体;作者主体意识与秦岭文化精神的神性相遇,也让秦岭与作者本人在情感、精神、灵魂上相融相通、互相映照,成为相互塑造、互相提升的同一生命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不仅认为《秦岭记》是关乎秦岭和作者本人文化精神世界的灵魂性书写,而且由于《秦岭记》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全方位诠释与本体性呈现,我还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贾平凹是当代中国一位在精神与灵魂上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且对中国文化传统有切肤体会、深刻认知、真挚感情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作家。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