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靠山》是一部着重反映革命年代人民群众支前事迹的报告文学作品。其有意在传统的写作秩序当中另辟新路,掘发遗落的“集体记忆”,为过往留存证言,为记忆重新赋形。作品借由重构革命历史的“行为”,不仅以“在场者”的姿态重建起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更得以生成一种返观历史、理解当下的“认识性装置”。因而,《靠山》亦是考察报告文学的一个样本,显示出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德性与可能。
关键词:铁流 《靠山》 行动 民间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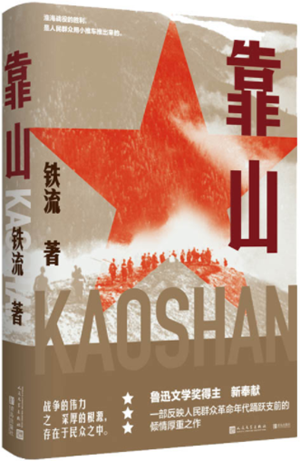
《靠山》,铁流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诞生算起,中国报告文学已然有百余年历史。然而,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相比,报告文学并非是一种主流文体,也不是一个热点或大众性文体。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动以及文学的边缘化,报告文学一度被认为正在面临“退化”“枯竭”或“尴尬”。这当然值得商榷,但同样不应被忽略的或许更在报告文学创作自身。作为集真实性、新闻性与文学性于一身的文体,其不仅是报告的“文学”,也是文学的“报告”。报告文学如何处理回应现实与关注自身的关系,即“精确地描述真实,而又不丧失作品的神韵和形式”,依然是其面对的重要课题。显然,这既是报告文学作家自身必备的能力,也是内含于时代发展逻辑的个体意欲借由文学这一介质回应现实的必然要求。
作为一名在报告文学领域深耕多年的作家,铁流始终坚守本心,以书写“时代报告”的使命和担当去回望历史、凝视现实,并在不断的书写中为时代提供一份份记录与证词。检视铁流的报告文学创作,从《一个世纪之交的话题——中国“标王”的背后》《支书与他的村庄——中国城中村失地农民生存报告》到《中国民办教育调查》《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等作品,既记录了时代转进中的“痛与爱”,也显示了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能力和品格。历经14年精耕细作的《靠山》,更是铁流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全新超越。作品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到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为经,以沂蒙山区以及其他革命老区为纬,铺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群众支前画卷。正如铁流所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就像打一口井,井打得有多深,水就有多甜。”铁流以此为起点,以“行动者”的自觉与敏感,不仅以“在场者”的姿态重建起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更为我们理解当下时代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可以说,《靠山》不仅标志着铁流的报告文学创作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达到的新高度,无疑也显示了当下报告文学创作的德性与可能。
一、“行动”的“艺术”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舶来”的文体,自“诞生”之日起,即要求“以行动的方式去记录、反映外部世界”。因而,在这种带有极强主动性与倾向性的“规定”中,无论是报告文学作者还是报告文学本身都被赋予了“行动”的意涵。不仅如此,在不同时代语境的召唤与重构下,尽管报告文学的边界与形式或存在错动与变化,但“行动”却始终作为一种显豁的表征与报告文学发生着关联,乃至成为报告文学得以有效存在的功能性因素。然而, “行动”本身并不能直接捕捉世界的“真实”,其逻辑进路在于以“行动”及其文学形式生成具有现实意涵的“艺术”。由此,不禁要思考的是,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代,《靠山》在铁流重返历史的“行动”当中,如何创造“时代”的“艺术”?
《靠山》不止于传统的书写秩序,而着眼在革命年代“被遮蔽”的历史与群体。一般而言,报告文学着重关注现实题材、重大题材,《靠山》却并非如此,其主要表现革命年代人民群众的支前事迹。近年来,革命战争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并不少见,如王树增的《长征》《解放战争》,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中国1946》,徐怀中的《底色》,彭荆风的《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等,但通过报告文学的形式,史诗性、大跨度地表现支前题材的作品却屈指可数。因为相对战争本身而言,“支前”可以说是“幕后”行为,而不是战争的“前台”。所以就题材本身来说,《靠山》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范围,具有不可忽略的艺术价值。再者,《靠山》塑造了一群幕后英雄——最普通的百姓形象特别是妇女形象。正因“从来战争史总在记录‘战役’和‘指战员’,女人在如此记录中难寻踪影;总结战事一般只看前方胜负,不计后方功过,女性的行踪因此消失殆尽……”,所以与其他报告文学作品相比,《靠山》也就构成了某种不同的意义与景观,其将以往习焉不察或无意忽视的部分重新编码,并以别样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一“选择”本身自有其明确的目的指向,即借由打开“尘封的故事”的“行为”,为当下的时代寻求新的经验和启示。因而,作品选取的角度、展开的方式、刻画的人物、坚持的立场乃至秉持的史观,无疑都共同指向了一个鲜活的时代理念——“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靠山》是以文学回应时代的又一次证明。
作为“行动者”的铁流,深知报告文学的合法性在于其所兼备的真实性与文学性,所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亦是其无法绕过的问题。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本不易也不可能做到完全还原真实,但铁流凭借长时间的细致走访调研,还有文献资料、历史实物的分析考证以及对历史发生地的实地体验,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真实性”的获得,并在主导性的全知全能的叙述中,得以还原出相对全面客观的“历史现场”。可以说,《靠山》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过往的革命历史,增强创作主体的“在场感”,力求尽可能地抵达历史的深处。然而,报告文学不仅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报告”,其终究也是“文学”。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文学的革命性,只有在文学关心它自身的问题,只有把它的内容转化成为形式时,才是富有意义的。因此,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也就是说,报告文学尽管首先在“报告”,但作为文学的一种体式,“文学性”仍旧是报告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由此报告文学才能够实现“政治潜能”与“文学形式”的自洽。
《靠山》的“审美之维”,首先在于选取的虽然是革命年代的支前题材,但这个相对“边缘”的题材却并未丧失“重大性”与“艺术性”。作品中无论是苏区历史、长征历史,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不仅在民族解放的历史脉络中凝塑成共同的文化记忆,而且形成以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沂蒙精神、抗战精神等为代表的红色革命精神。同时,其也内化于20世纪整个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成为全人类的精神遗产。其次,铁流“本着要写得‘好看接地气’的原则”,“努力从人性、人物内心世界着手,着眼于细节,力争用文学的语言来叙述真实的故事”。《靠山》中,不管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刘长秀、徐解秀、王换于、戎冠秀、刘桂芳,人物语言不仅合乎身份符合情境,甚至说话的声调与语气都活灵活现。如“长征前夜的故事”一节中的新娘刘淑芬,从与红军丈夫肖文童见面前的焦灼期待到见面后的温存幸福,再到得知丈夫即将离开苏区时的万般不舍以及最后分别时的情凄意切,这些通过对人物动作、对话语言和所处环境的细致营造,便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复杂立体的女性形象。值得注意的,还有铁流对历史事件所涉地区的习俗仪式、地方风物的描写与呈现,这些带有“陌生化”审美效果的“风景”,在还原历史真实性的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与可读性。如在“发兵山东”一节中,就详细描写了王换于一家深夜为八路军同志做煎饼的过程。不仅为我们呈现了沂蒙山区普通百姓带有人间烟火的日常生活,更显露出其中所蕴藏的沂蒙人乐观热情的文化性格。
可以看到,《靠山》无论在题材的选取还是对象的呈现中,都时刻秉持“行动者”的理性思索与人文关怀。但铁流之所以有如此的意义,显然不只在作品本身,而是意图以“行动”的方式将那些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风景”,重新放置到我们面前,并在带有某种美学意味的文学创造中,重建“我们”与“时代”的关联。
二、民间立场:以人民的名义
区别于其他文体,报告文学的最大优势就在对时代现实即时且真实地艺术性展现,这也决定了其可能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作为“行动”的艺术的合法性前提。而在真实性与艺术性的耦合中,必然亦牵涉到创作主体的价值立场与情感倾向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怎么写”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写什么”与“为谁写”的核心问题。因而,如果说《靠山》有意回避被主流热衷书写的现实题材、热点题材,以返观历史去呈现其中更为鲜为人知的一面,那么铁流的“行动”则势必关联到其如何看待本人这一“选择”。日本学者川口浩曾说:“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绝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于铁流而言,如果说“目的”指向“写什么”,那么“倾向”则无疑是“为谁写”,即如何将人民的名义作为书写的“动能”,在叙述中自觉地秉持民间立场。
相较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靠山》尽管把创作的视域同样放置到革命历史当中,但因其选取的视点与姿态的特殊性,使其得以在边缘性的位置上生成具有异质性的文本。其首先体现在《靠山》对“英雄”这一能指的处理当中。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被指称为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中,有不少是革命英雄传奇,在这些作品中“‘英雄’是一种等级性关系中的存在,他们是‘非常人’”,因而往往具有某种神秘性、传奇性,甚至被神化为无懈可击的存在。但事实上,在他们的整体创作中,反映出来的往往是“英雄创造历史”,而非“人民创造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人民”的名义讲述,就成为《靠山》进入革命年代的内在动能与逻辑起点。尽管在长时间的书写跨度中,铁流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作了细致阅读、资料考辨乃至实地寻访,但其仍旧没有将未曾亲历的战争前台作为叙述主体,而是把视点转移到熟悉的沂蒙山区的农村,将战争的“后台”开辟为新的“阵地”。《靠山》中几乎没有中心事件与核心人物,而是在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基础上,使其显露出英雄主义意味的质素。可以说,《靠山》的关键之处在于,一方面将以往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予以“泛化”,另一方面则着力发掘人民身上独特的英雄主义元素,以构筑英雄—凡人—英雄的结构性关联,并借以形塑具有英雄主义气质的人物群像而非孤立超拔的个体英雄。如作品中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物的描写,并不是先入为主地将他们作为伟人或领袖去书写,而是以平视的目光去看待他们,在不有意拔高人物形象的前提下亦避免了类型化或概念化“英雄”的出现。作品的可贵之处,很大程度上也正在对革命年代人民群众一往无前的支前事迹的重新检视与呈现中。文本中虽然没有一以贯之的主角,但全书凡六章,每个小节都借助特定事件集中围绕数名人物展开,而他们大多是普通战士或寻常百姓。铁流正是通过对他们普通但绝不平凡的事迹予以开掘与展现,诠释潜藏在“凡人”身上的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英雄主义精神。总之,《靠山》不仅将“英雄”放在了新的脉络中进行观照,更赋予了其全新的价值内涵。
《靠山》在历史叙述中通过民间视角重构“英雄”意涵的“行为”,是借助“人民”这一主体得以实现的,其中尤其得益于对众多女性形象的着力塑造。事实上,“战争于沉睡千年的女性生活可以说是一次变革的契机”,“无论底层或中上层妇女,无论她是文盲还是知识女性,都有可能通过‘参战’走出家庭、走上社会、走向‘解放’,成为世界范围女性社会参与的独特风景”。显然,在革命战争的历史语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靠山》中的女性人物在行动上大多不再满足于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存在,而是纷纷“抵抗”以往的“禁锢”以寻求自身的“解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众多女性不仅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变化,甚至开始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并扮演某些主导性角色。然而,这种“解放”无疑也是有限度的,就像“王换于虽为内当家,可这位出生在清朝末年的女人,骨子里很传统,在她内心深处,她还是把于泮尊为当家人”。可以看到,铁流在作品中有意激活她们具有主体性的一面时,也时刻不忘尊重现实,直陈她们心理与性格中的弱点与缺失。此外,《靠山》在人物塑造上,不仅着力于性格刻画的真实立体,还旨在形塑一组散发着人格魅力的女性群像。其中,有因长征时期与三个女红军许下约定而守望50多年的徐解秀,有为维护革命大局而大义灭亲的傅玉真,有抗战时期创办托儿所抚养革命者后代的王换于,有精心照顾负伤八路军战士却全家节衣缩食的祖秀莲,有为拯救负伤缺水的伤员而奉献乳汁的明德英,有勇救伤员、发展生产与支持前线的戎冠秀,有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妇女同志用肩膀为战士们搭建“人桥”的李桂芳,有“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支援前线”的董力生……作品当中,众多闪耀着光辉的女性形象纷纷从“后台”走向了叙述的中心,她们或许在身份、年龄、性格与经历上存在差异,但无疑都是革命年代富有民族精神与人道主义情怀的底层英雄。尽管她们每个人都是远离“宏大叙事”的普通人,但在硝烟弥漫的血与火的年代,却共同选择用个体的力量构筑起战场之后的防线。正如孙犁笔下以水生嫂为代表的乡村女性们一样,“这类人物形象除了政治层面上作为毫无保留地支持、奉献民族、阶级解放事业的‘人民’意象外,更多地作为家园(母性)、民族传统、人性美的意象而获得广泛传播认同”。不同的是,铁流在显示这些女性们所具有的力量与品质的同时,并没有选择刻意回避她们生存的苦痛与艰难,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亦触及了她们“觉醒”与“解放”的限度和难度。
三、“对话”的文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报告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被指认为以文学的形式即时参与现实问题的“文学轻骑兵”。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在直面现实的同时,亦开始返观历史,这在题材的延展中自然也引发了创作观念的变革。有论者曾将此类题材的报告文学称为“史志性报告文学”或“史传报告文学”。然而不管何种概念或指称,无疑都指向对历史题材进入报告文学创作的合理性的理性论证与情感认同。就如铁流所说:“新时期以来,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读者从他们的一部部优秀作品中,读到了重大事件,读到了历史的震撼,读到了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其显然亦成为铁流将历史与文学予以复合的“方法”,即秉持民间立场以人民的名义去记录、见证与言说。更重要的是,历史叙事往往并不是作家乃至报告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其根本更在于如何借助对历史的激活去为现实提供新的可能与启示。关键的是,现实需要既是报告文学深入历史的起点同样也是终点,只有将历史与现实建构起有效的关联,报告文学才有生成“对话性”文本的可能,历史也方能真正获得重返与照亮的意义。
就报告文学本身来说,题材是否具有“即时性”或“新闻性”并不必然牵涉到其最终的现实指向,因为即使是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通过创作主体对历史资料的开掘和处理角度的更新,也可以提供以往作品所没有涉及的某种“新闻性”因素。问题在于,作品当中是否最终有效生成具有“现实感”的时代形式与精神内容,而这显然亦是《靠山》的题中之义。铁流在创作过程中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并对革命年代的历史亲历者及其后人进行细致详尽地采访记录,其不仅为文学创作积累可靠的资料素材,更是对过往鲜为人知的历史的抢救性发掘与整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靠山》不只是一部恢宏厚重的报告文学作品,更是一份具有历史“补白”意义的史料文献。也正因此,《靠山》才得以无限逼近历史的本真,并在历史叙述中获得极强的“在场感”。然而,报告文学“不仅在于向人们报告生活中曾经发生什么,存在什么,可以而且应该超越生活,使读者从个别人的命运中,从社会一角中,窥见历史的生动画面,聆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不难看出,铁流亦不止于提供一个具有“新闻性”的历史故事或为一群被无意尘封在历史地表之下的“小人物们”形塑群像,其更在于从历史当中为我们寻求某种精神资源,以及理解时代与现实的普遍性经验。
尽管《靠山》所叙述的革命年代是过去的历史,但历史在不同时代的建构与重构中无疑是具有延续性的。如阿斯曼所说:“社会需要‘过去’,首先是因为社会需要借此来进行自我定义。”所以“过去”对于“现在”来说虽然是“旧的”,“现在”却要经由“过去”才能得以“定义”。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就是“集体记忆”,其“作用范围包含两个方向:向后和向前。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可以看到,《靠山》作为向建党100周年献礼的作品,无疑扮演着纪念性文本的作用,其正是借助对历史的重返与叙述试图建构与重构“集体记忆”,为国家历史保存不灭的火种,为民族意识积累深厚的文化养料,为当下的时代需要提供新的精神资源。作品以“在场”的姿态去描绘战争幕后的“小人物”,细致刻画他们在残酷的战争当中所作的历史抉择,而也正是从构成历史基底的“小人物”身上,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另一种样态与真实。此外,在对作品人物的勾画中,铁流不仅为其补上“前史”,更会适时穿插此后的“现实”,在完善人物性格与心理发展逻辑的同时,也极大地激活了人物与事件的现实意义。而《靠山》在对革命年代的人物群像及其英雄事迹的还原与诠释中,亦成为一个跨越历史的“隐喻”,从中我们得以看到人民群众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靠山”。由此铁流也实现了从民族历史当中掘发遗落的“集体记忆”,并完成以“支前精神”为代表的“民族精神”的获得与更新。黑格尔认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靠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史”与“诗”的有机结合,并将日常人性的光辉与革命的庄严感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现代意蕴与审美景观。
与小说创作相比,作者的主体意识在报告文学中将会得到更加显豁的表达。正如巴克所说:“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的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报告者的意识上。”这无疑也为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如何自觉地审视历史和回应时代的深层关切。尤其对于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来讲,主体意识很大程度上即反映在创作者的历史理性当中。波兹曼亦曾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的论断,推及报告文学,则不难看到创作者历史理性精神的强弱有无,将会直接与作品中的思想性与可信性产生关联。进一步来说,作品所承载的意义与启示也必将随之获得或失去应有的有效性。反观《靠山》的写作,尽管着眼的是作为“前史”的革命历史,但在角度与对象的选取上却体现了当下时代的某种诉求。其有意回避已被反复书写的战争前台以及全能式的英雄,转而为“小人物们”及其支前事迹立传,并以此回应当下社会对于个体价值的尊重与肯定,强化了时代理性与民族精神中对“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认同。
作为一种带有导向性的文体,报告文学势必要自觉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并以艺术的方式,或建构整体性的社会价值认同,或揭露社会转型期的重大问题。但“艺术品不是历史教科书的图解,它需要从揭示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由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活动中,展示历史的内容”。这也是《靠山》在历史叙事中,不仅张扬革命年代支前群众与革命者“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一面,同时直面他们对所处现实情境变换的疑惑与不解的深层原因。如“子弟兵的母亲”一节中,曾经踊跃支前照顾伤员的戎冠秀,因为土地增加,由贫农变成了中农,但在得知因此不被允许参加党员会时,她百思不得其解,丈夫李有也发出“革命革命,到头来怎么还革到自己头上来了”的疑问。虽然这种困惑很快就在“放心吧,毛主席不会不管的!”的自我宽慰中结束,但还是多少透露出了创作主体在现代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的烛照下,对过往历史变动所造成的现实问题的审视与反思。可以看到,历史不仅有顺势而下的浩浩汤汤,也有逆流翻涌的波动回旋,唯有坚守历史理性方能思辨性地看待历史,并建立起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关联。“因为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所以铁流在创作中将个体与民族、历史与现实、思想与艺术有机融合的努力,就显得难能可贵。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将《靠山》生成为一部具有“当代性”的“对话”的文本,升华了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的时代价值与艺术品格。
《靠山》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真实性与艺术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其有意在传统的写作秩序当中另辟新路,选择“边缘”的视点深入历史,并自觉地站在民间的立场之上,用艺术性的方式还原革命年代人民群众的支前事迹,借以重绘革命的历史图谱,为过往留存证言,为记忆重新赋形。而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当中,无论是对遗落的“集体记忆”的掘发,还是由此而获得更新的民族精神谱系,都显示了铁流着眼现实,为所处时代寻求新的启示与意义的不变本心。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融合了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靠山》,无疑是铁流将“文学”作为“方法”,以“报告”作为“艺术”,在激活当下报告文学创作以新的可能的同时,以“行动”回应时代深层关切的又一次超越与证明。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显然,作为“报告”的“文学”,从来都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其往往与“时代”共同分享着带有现实性的论题。而也只有在对时代现实的切实观照中建立起文学与现实的关联,其才能够成为“及物”的存在。由此,《靠山》不仅可以看作铁流借助报告文学的形式构建某种时代美学的尝试,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们返观历史、理解“现实”的一种“认识性装置”。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