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后作家访谈
作为加缪的迷恋者,阿乙曾尝试着将自己的故事写得像那位存在主义大师一样冰冷、阴郁。他的小说多以侦探小说的形式呈现,其间不乏阴冷血腥的凶杀场景,但并不侧重展示依悬疑而设的离奇案件,而是透过事件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
迄今为止阿乙已出版《鸟看见我了》《阳光猛烈万物显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情史失踪者》《早上九点叫醒我》(译林出版社)等作品,最近又出版了短篇精选集《五百万汉字》。自2015年将海外版权签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后,短短两年之内阿乙的作品已经输出了7个语种15个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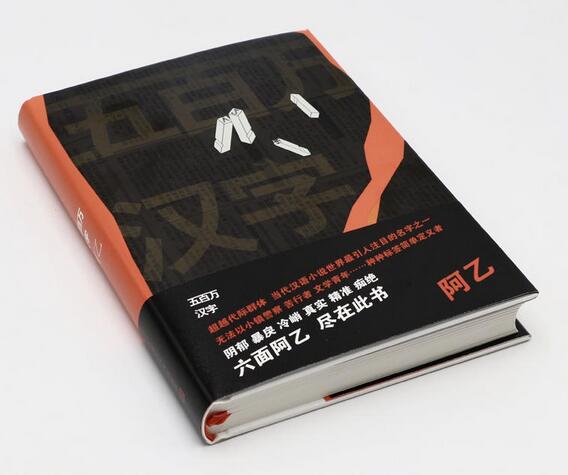
《五百万汉字》,阿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48.00元
从《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开始,阿乙就在抵抗空虚和无聊。“如果没有写作,我将被每天到来的凄惨的黄昏给扼杀,给镇压,变成一个无所事事,欲哭无泪,只待死神来收走的畸零人。是写作和婚姻使我正常。”阿乙说。对于帮助过自己的所有亲友和老师,他始终充满感念。
中华读书报:从小学时就开始发表作品,那时候是否已显现出某些文学天赋?你的父亲给你们兄弟三人设定的人生方向,也还是有依据的吧?早期的文学爱好缘自什么?
阿乙:我的父亲是这么设计的:长子学理,次子学文,幼子文武双全。父亲是有强力主张的人。我们三兄弟就是这种教育的结果。我后来对父亲有所违背——从公务员岗位脱离,去外地报社上班,进而职业写作——实际是我还在坚持文学理想,而我的父亲想对我进行矫正,因为他从小鼓励我做文学家,但是后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奢侈的梦想,他觉得让我做一个公务员对家族更好,对我自己也更好,也切合实际。直到后来我在文学上取得一点成绩,才部分扭转了他的看法,也部分扭转了家乡人对我的看法。这是基于一种名声的考虑。名声使我逐渐在他们的心中权威起来。有一点小名声是我和故乡重新融合的基础。小时,父亲为我订了《小主人报》,他鼓励我投稿。我投文摘稿,叫《汉字知多少》,多年后,我写了一篇小说,叫《五百万汉字》。
中华读书报:在警校读书、从警,对你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你如何评价那几年的经历?
阿乙:我在毕业以后做了五年警察。我现在倒不后悔这一段经历,因为写作的大部分资源就是这一段时间积累的。从考上大学的18岁开始,我一直不怎么学习,直到26岁,有一个朋友批评了我,或者直接说他讥讽了我,我才手不释卷,直到如今。我生活的时候生活得很激烈。读书的时候读得很刻苦。像是一匹傻马,就是在平地上走,头也是点来点去的。
中华读书报:你的写作路数,迥异于同时代的多数作家。在我有限的了解中,很多人是从“我”的经历和经验写起,甚至就是自传体的小说。我很好奇,从一开始你就呈现出相对成熟的写作技巧。
阿乙:因为在动手写之前,我有计划地阅读了四五年的外国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基本上的选本都有读。对短篇领域的一些结构上的探索、意识上的一些革新有一点点研究。可能就是这些准备让我显得不太怯场。我一直关注国内外文学的新进展,特别是非虚构的发展,我对新的事物比较敏感。但我并不盲从一些新的探索。可以说,如果没有一个先进的办法,先进的结构和先进的叙事方式,那么一个人拥有再好的资源,他的资源也可能被浪费掉。先进的方式可以拯救陈旧的叙事(我很同意博尔赫斯经常强调的观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讲述的,所有的讲述都是再认识,所有的讲述都是重复讲述),陈旧的方式可以败坏时代好不容易吐出来的新鲜事物。另外我会阅读一些优秀批评家的引导性文字。国内的李敬泽、谢有顺,国外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一封信》、博尔赫斯文论、普利策奖得奖作品、纳博科夫文论、卡尔维诺文论,及后来读到的布鲁姆、伍德。
中华读书报:当然,《情人节爆炸案》是个例外。小县城的压抑、失败的恋爱……这些都能看到你的人生经历。《模范青年》也是个例外,有很强的自传性。总体上,你的写作有一股狠劲儿,被不动声色地藏在故事里,藏在平静的叙述里。谈谈你创作素材的来源好吗?处理这些素材的过程,你一般会着重考虑哪些问题?
阿乙:谢有顺在《成为小说家》里提过“地方”这个重要概念,也就是作者要有自己的根据地,有一块像福克纳笔下那样的邮票大地方。要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成熟的作者都会耕耘自己的经验。警察生涯和县城经历是我唯一能掌握好的东西。这些是闭着眼睛可以写出来的,堪比血肉。所以我的小说多半是用一种新奇的或者是新鲜的结构,来书写县城的生活,来书写压抑的小城人,来书写一种科技时代的遗弃人。写作一旦离开县城让我感觉无所适从。这些年,大概有十四五年,我一直在城市生活,根本写不出城市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还是博尔赫斯说过,作者最熟悉的就是他的童年。我的童年就是在乡村和县城度过,我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城市。失去了北京上海和纽约,失去了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情人。
另外,像一本叫《人类酷刑简史》的书说的一样,人口的过剩导致了匿名化,羞辱或耻辱感失去了它原有的威力。我是这么来理解这句话的,像马尔克斯《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这样的文学,在城市的环境里瓦解了。彻彻底底地瓦解了。人类已经没有那么强的道德敏感性。《情人节爆炸案》这篇小说随着时代和人心越来越宽容,也越来越失去了它的震撼性。
中华读书报:在意识到自己成为“作家”之后,你的写作和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吗?
阿乙:我的写作变得更自由了。时间得到了保证。但是,我也参加了太多的活动。给自己和别人频繁出台。我很难开口拒绝人(虽然还是拒绝不少)。有一些朋友警告我,一个在活动中频繁出现的阿乙,不是他心目中的阿乙。听到这样的话,我总是不快。那是隔了几天我就很感谢了。因为我确实意识到,这也是我内心感到有负罪感的一部分。只是我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教导而已。朋友说的都是对的。可能是这一代的写作者比较少,所以人均出场率比较高。我得想想办法。因为一个作家的权力在于他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五百万汉字》,集中了你的十二个短篇,以经验、志异、痴人、概念、技法、元小说分为不同类别。这样分类科学吗?划分标准统一吗?你觉得能够涵盖自己的不同风格吗?
阿乙:我请了北师大的文学博士徐兆正来替我作出选择。我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判断力。我相信有水平的他者。他的选择很好,分类清晰。他对我的解读也让我有很大收益。主要是他对我作品赋予的热情,让我感动。
中华读书报:你总在尝试以不同的风格创作,这种尝试都成功吗?是否也会有不满意的作品?
阿乙:我很羡慕那些一两年写一部长篇的作家,他们就像是铁路线上的火车,找到了运行的规律,有节奏,不会衰竭。而我只是写了一部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资源的矿产就挖空了,整个现场只剩一片废墟。已经没有重建的可能性。我上一部写得长的作品只有5万多字,《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其内容与《早》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是关乎到人生态度,一个就是对乡村的画卷式描写。
正因为很容易把自己写枯竭,所以我到处突围。我是那种生态破坏型的写作者。我还会在别的题材做出尝试。因为我自己也喜新厌旧,见异思迁,不想就一个题材重复地写。也是顺势而为。因为确确实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长久的经验系统。我得去找矿。
中华读书报:写作多年,你觉得自己的创作风格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阿乙:从语言结构内容思想到创作观都在改变。我一直在变化。这是我在文学领域内变化。我不会别的,连简谱都不识,很多植物名字也叫不出来,所以没办法往文学领域外突围。我试图去写剧本,感谢导演不喜欢。我自己也不喜欢。把这条路走死了对我有帮助。
中华读书报:听说你对自己的小说没有一个是非常满意的?你在创作中遇到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怎么解决?
阿乙:我有一种完美主义倾向。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强迫症。非常非常的糟糕,直接导致了我生病。我写小说时总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犯一些错误,害怕一个错误导致自己的一切都会毁灭。格非先生和金宇澄先生我都请教过,他们都认为应该给自己一些犯错的机会。没有错误就没有正确,没有先就没有后。现在我已经减少了修改的频率,不会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过于疯狂的修改。我认为用电脑写作,也鼓励了作者反复修改,因为修改是那么的方便,所以作品总是不能成形。要自信!我现在常这么说。但有些毛病是从小就犯下来的,因为我的父亲总是对我不满意,即使他对我很满意,他也会在嘴上不满意。他过世了,这种控制似乎还没有结束。
中华读书报:一般作家写到一定的程度,会尝试用长篇证明自己的能力或文坛的地位。你是怎么想的?
阿乙:我有写长篇的愿望和理想。但是这一部长篇是顺势而为的。是我用短篇和中篇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一次写作的规模,索性就写成长篇。办法用的还是写短篇的办法。密度特别的大。我羡慕那些写出成熟长篇的作家。他们的力气和我是不一样的。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在文学创作上所受的影响?
阿乙:国内主要是受先锋作家的影响,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等。我喜欢他们在年轻时代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彻底改变了汉语文学的思路,可谓是点亮了灯火,开拓了道路。很难想象,没有他们的话,我们难道还要去继承伤痕文学吗?
我受国外作家影响比较多的有:卡夫卡、加缪、昆德拉、博尔赫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威廉·福克纳、普鲁斯特。昆德拉是容易被低估的。采用的视角是上帝视角,这个几乎每个作家都会,但是他的独创性是,总是能写出两个人在意愿上的不协调性。人和人是背离的。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你近期的写作计划?
阿乙:最近在写一些小叙事小随笔。试图恢复短篇写作。上一个十年,从短篇写到长篇已经结束。下一个十年,迟迟还未开始。也会是从短篇写到中篇。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