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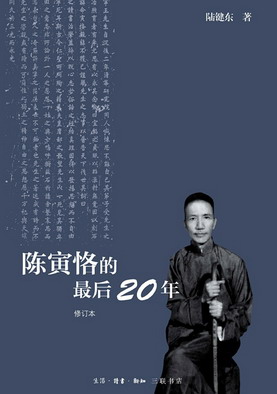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陆键东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对一个文化符号心怀感念,抱有期待,是当下再常见不过的现象。也许是现下还未产生足以替代记忆里佳作的经典,也许是现实中过多的不确定使往昔显得尤其美好,于是最新电影要搬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曲装点门面,中学生素质教育要抬出民国教材当独门法宝,就连阐发政治见解也要祭出儒学来做药引子。
图书出版领域也未尝不是如此。1995年,《陈寅恪的最后20年》(以下简称《20年》)横空出世,一时洛阳纸贵,也将陈寅恪的名字从学术圈推向公共领域。当此书的修订本问世时,很多读者颇为关注,希望能从修订本中体会到当初阅读初版时的感动。
这个修订本的问世,距离初版已有十八年。这十八年中,陈寅恪的形象从学者到士大夫,从独立的思想者到中国文化的象征,愈来愈被放大,愈来愈被神化,这和《20年》引发的连锁反应不无关系。《20年》的作者陆键东在修订本“新版前言”中也表示,此书出版后所引发的陈寅恪热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现象,此言不虚。在《20年》出版后将近十年间,知识圈以为谈资,有些论者对此稍有警醒,忧虑地提出“劝君莫谈陈寅恪”,就是怕陈寅恪被过度诠释,成为远离本相的虚幻偶像。
当年,《20年》如一只扇动翅膀而引发风暴的蝴蝶,除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本位主义抬头这一可以孕育风暴的气候因素之外,作者的叙述方式与笔法正如蝴蝶之翼。陆键东站在了陈寅恪的立场上,试图用陈寅恪的视角去看待1949年起的风云变幻对陈寅恪以及陈寅恪在内的知识阶层的学术生命与个人命运的作用,以议论和抒情表达了对陈寅恪的崇敬,对其晚年遭遇的哀痛。这种叙述视角以陈寅恪为基准,将与陈寅恪晚年有交集的学术与政界人士、学生与同事都放在一个参照系内,鲜明地将这些人物划为与陈寅恪立场相近、相异、相反的几类,相近者多加褒奖,相反者略有微词,相异者如陈氏旧日爱徒汪篯则抱以同情地稍作批评。若不去深究真相如何,这类文学性极强的臧否文字,颇有激浊扬清的味道。
视角不可能完全重合,所以这种视角的选择很容易造成过度诠释,也会让作者不自觉地神化传主。不过,在社会对陈寅恪普遍缺乏认识的九十年代中期,《20年》这种笔端常带情感的基调、以陈寅恪的角度解读共和国前二十年的政治与文化政策的叙述方式极富感染力,这也是该书的影响长盛不衰的魅力所在。
值得反思的时代、值得关注的人物、报告文学式的书写体裁、在大量采访与档案调查基础上的叙述,加上在当时而言立场独特的评论,使《20年》在20世纪90年代的书林中鹤立鸡群,虽有模仿之作,但也难兼具《20年》的这些特色与长处。
十八年后的修订本,延续了旧版的风格,议论与抒情的段落依然饱含情感,在一些措辞上稍作调整,整体基调则依然如前。从修订本的整体结构来看,并无章节方面的大幅调整,只是在一些细节内容上修改、扩充或增加注释。这种做法是明智的,作为广为人知的一部作品,原作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文本,若全部重写便已成了一部新书,更何况在陆键东看来,原作的评述之语与视角选择自可成立,并无“重写”的必要,此次修订只需做拾遗补阙的工作即可。
这个修订版本,对新读者而言仍具吸引力,而对旧版读者以及对陈寅恪有所了解的人而言,则未为尽善。十八年间,叙述与专论陈寅恪生平、思想与学术的作品愈来愈多,无论在材料的丰富性上还是分析的深度上都远非当年的同类书籍可比,走向专业化的陈寅恪研究,也给修订本《20年》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如何对这些年陆续出现的成果进行吸纳与回应?
作者尽其所能做了努力。在修订本的参考书目中也列出了一批近年的研究成果,如资料性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回忆录性质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史学思想研究性质的《陈寅恪史学述略稿》,事实考证性质的《陈寅恪从考》等。依照以上各类新出著作,陆键东试图令修订本中的文学色彩减少、学术色彩增强,但在叙述视角与基调确定的情况下,这种尝试似乎颇为吃力。
以陈寅恪的角度思考问题难免造成不及兼听。先入为主的立场是感性的历史讲述者难以避免的倾向,如果不能将视野投向传主所在的整个时代,将人物放置其中进行讨论,主观性就会越发强烈。作者在修订时所选取的一些参考文献,多有带着“温情与敬意”对陈寅恪进行论说的倾向,极具情感的文字与作者选定的参照系相结合,似乎就使陈寅恪的形象从一个具有个性的学者提升为一个几乎不犯错的完人。作者自己也注意到晚年的陈寅恪比较情绪化的事实,发论时却每每以陈寅恪之是非为是非,使自己的叙述也有些情绪化的色彩。
做人物之研究,应有的立场是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不能将审美与求真混淆。《20年》最大的问题,就是灌注了太多的情感,对一些现象“信以为真”。比如陈寅恪的政治立场几次被评定为“中右”,作者就认为在上级主政者都明确表示要保护陈寅恪的情况下,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主持者依然持此论而不改,应是有意为之。至于为何中大历史系会如此评定则缺乏进一步的分析。事实上,若要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上重新论证,则不止这一具体问题,很多议论性文字都必须重写,如此一来,可能真的要出现一个与旧版截然不同的《20年》了。况且,选择以研究对象的视角为自己的论述视角,本身就是很危险的。如果材料不够充分,不能让具有各种倾向性的材料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很容易变成一己之见的自言自语。
平心而论,《20年》出现的这些遗憾,并不掩盖其应有的价值。作为一个有关陈寅恪晚年生活、思想与学术的文本,十八年前的《20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寻找档案,查访与陈氏有交往者,钩沉索隐,实属难得,此书推开了对陈寅恪晚年、对一代学人在一个全新时代的经历的研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
如果我们将这本书作为一个时代的标记,就可以发现,这十八年间,不但有关陈寅恪的书籍越来越多,一些对于书籍而言至关重要的条件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年里,出版机制的变化让书籍问世的速度越来越快,书籍的总量也以几何级数增加,这种状况让图书世界出现了相对饱和;网络媒体每天都喷射出大量讯息,而且日渐成为我们获取资讯的主要途径,使纸质图书的饱和感越发严重。在此种环境之下,如果没有独占性的资源,无论是资料的稀缺还是评论的个性化,都难以让读者和评论家满意——这还只是就健康的书籍而言,不包括那些追求噱头和迎合读者的读物。
除去这个环境因素,严谨的学术写作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十八年前,用《20年》的容量写完陈寅恪的晚年是绝对可以的,但随着资料刊布越来越多,每一个具体事件、每一个与陈寅恪有关的人物可书写的空间都大大增加,再以原来的篇幅综论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经历,难度几近于挟泰山而超北海。在有关陈寅恪的图书题材已涉及到各个方面的情况下,再为陈寅恪的后半生做一部通论性的作品,莫如将论述时段拆分,或是只谈某个领域。在这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新出版的《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就选择了一个全新的主题。此书只选择了陈寅恪前半生中的一个时段——留学时期,并选取了这个时段中的一个侧面——学术思想的渊源——进行研究,但这样就已使其著作的篇幅超过了《20年》。所以,《20年》在十八年后的修订再版,确有与当下不合之处。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