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洁非,学者,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室主任。多年从事文学史研究,亦以明史方面著述见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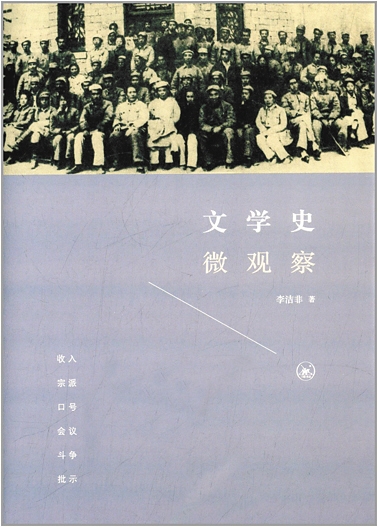
《文学史微观察》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8月
2014年,学者李洁非出版了新书《天崩地解:黄宗羲传》和《文学史微观察》。写作时,两本书穿插进行,内容也出现交互,着重史实的风格一以贯之,更重要的是,在李洁非看来,从明代至今,中国始终是在完成同一个主题,即社会转型。
《天崩地解》后记中,李洁非写道:“中国真正交其‘大壮’之运——以今天话讲是实现向开明社会的进化——这将是关乎根本的环节,有巨量的工作在等待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明史研究,还是当代文学史研究,都是李洁非为这一“关乎根本的环节”做出的努力。
谈新书创作
当下对史料运用既很不够,也不怎么好
大学时,李洁非喜爱戏剧,临近毕业,他打算做这方面的论文,选择以晚明两位戏曲大家汤显祖、沈璟之间的一场论争为题。那时,他对明代思想文化没有多少了解,不曾想,兴趣也从这里被激发。
“我意外发现明人的想法、观点以及精神氛围,离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像并不遥远,甚至给人共鸣,于是大有兴趣。”李洁非对记者说。1982年,他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坚持长年阅读明代文史。慢慢地,朦胧的兴趣形成一个明确的历史视角——“就是从中晚明到今天,我国历史应该说还处在同一个大的段落,问题相通,精神思想的格局也类似。”
历史视角的形成直接影响了李洁非的研究和写作,约从十年前开始,他沿着当代和明代两个方面同时推进。十年里,李洁非创作了十余本书,“关于当代和关于明代的,差不多五五开,各占其半”。今年,《天崩地解》、《文学史微观察》两本书出版,写作时并行完成,“可能上午写写当代,下午写写明代”。在李洁非看来,这种写作,不仅思考上有互相促进的关系,“行文上大概也彼此有所滋养、呼应”。
李洁非注重史实梳理,少做主观判断,这种学术风格从《解读延安》开始,到“典型三部曲”已臻成熟。对于当下研究者对史料的态度和运用,在《典型文案》后记中,李洁非痛陈道:“近三十年,有关当代文学的史料,出版与发表相当惊人,简直应接不暇。但与这种情形不成比例的是,用得既很不够,也不怎么好,就像应有尽有的各种建筑材料,堆放于地,随处散落,迟迟没有拿去盖房子。”另一方面,对于研究者惯于主观判断,他说:“几十年来,不论当代文学还是其他方面的讨论、纷争,判断过剩、主观过大,安于陈述事实者少。我因为个人有所反思,而力求减少主观判断,来努力接近客观。”
学术研究之余,李洁非喜爱欣赏书法,还喜欢阅读探案推理小说,对某个刑侦主题的电视节目,也能守时收看,其中的技术环节,如查找线索,专心验证等,他觉得“极具魅力,甚至令人痴迷”,因而“特别迷恋”。学者王春林认为,李洁非的非同寻常之处,正在于创造性地把司法断案与文学研究这两件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巧妙地勾连在了一起。
“探案推理小说隐含一种处事方式,一是思必有凭,一是看重细节。我觉得做好任何工作,都得如此。说到对探案推理小说的借鉴,在于它不靠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以精密叙事攫住读者,这也是我认为的历史叙事拉近读者的较佳途径,故而借鉴它。”李洁非说。
谈当代文学
失去了完整的独立性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专访他的报道中有一则写道:“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在《文学史微观察》开篇,李洁非以这一段为切入口,来考察当代文学史。
“写书有稿费”,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句话,在李洁非眼中,却道出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一大要点,“它约略可以表作:现代中国,文学成为谋生手段,作家则职业化;作品能够换取收入,收入环节也左右着文学所有方面。”这两点,都与晚明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文学史微观察》这部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中,李洁非提到,“中晚明开始可以找到一些文学商品化的苗头”。在他的笔下,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晚明史研究不时形成呼应,甚至两相交互。
“简单通俗地讲,‘古典’文学是写给自己的,‘现代’文学是写给别人的,前者是所谓‘垂文以自见’,后者虽然也含自我表现目的,但首先是面向社会、将产品供给社会同时以此来维持存在。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文学写作者的职业化,二是文学产品的商品化。我们目前的文学,概莫如此。”李洁非分析说。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宋元即已萌芽,“而大面积、明显、正式地形成其局面,是在晚明”。当时,阮大铖、冯梦龙及许多文选家,有意识地把文学作为商品经营且取得了成功。“他们可以说是现代职业作家的先声。”李洁非说。
文学商品化影响深远,市场大潮汹涌澎湃的当下,尤为明显。“文学纳入交换关系,或者说文与食挂钩、文学用来谋生,造成了文学对社会的依从、对金钱的依从、对政治的依从,包括对读者趣味的依从。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失去了完整的独立性,所以今天的作家诗人不要说和陶渊明比,即便想拥有苏东坡式的从容、自由与纯粹,也是奢望。”不过,李洁非觉得,保存文学的自主性、为它抗争,仍是文学根柢所在和不能放弃的使命。
现实给出的答案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一方面是依附的,一方面始终在反抗——反抗沦入彻底的不自由,不论是被政治所控制,还是被金钱所控制。
谈历史分期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应是1840年
李洁非坦承,他研究明史,“是为其‘古代史中的当代史’的特质所吸引”。当年写毕业论文时被激发的兴趣,早已成为自觉的学术追求。
在李洁非眼中,历史分期是史学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根据目前的历史分期,明代归入古代史,给人相隔遥远的印象;中国近代史以1840年为开端,以鸦片战争为标志。
“为什么?因为要给这段历史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的认定。就是这个社会性质认定,把近代史框死了,造成非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不可。实际上,研究中国历史主题和历史矛盾演进本身,我们觉得鸦片战争虽然无疑表现了中国历史已在‘近代’状态,但绝不能说是这段历史的开始。”
李洁非强调,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起码比鸦片战争早200年,“也就是说,起码可以推前至晚明”。当时,社会的具体表现有——“明季之世从万历以来,经济的发达、思想的活跃,与帝制晚期的社会政治形态之间,已构成绝大的苦闷,甚至当时人们已清楚意识到历史的阻隔在哪里。”
其中,关于中国面临自帝制以来一大变局的认识与诉求,被明明白白地提出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什么意思?很明显,这是把帝制的形成、产生及存续,完整地看成一个历史单元,称之‘一乱之运’,而他断言此一‘运’行将结束。‘明夷’两字的由来——‘夷之初旦,明而未融’,犹如我们现代人讲的‘黎明前的黑暗’。”李洁非解释道:“我们进而从黄宗羲抨击‘家天下’、倡人民‘敢自私’、主张‘公其是非于学校’(废专断为群议)等来看,他所向往的黎明,确与近代民主处于同一方向。”更重要的是,明朝落幕时人们看法很明确,国家并非经济落后,并非文化落后,而是制度落后——不够好或不够合适的制度有违正义,严重窒息了社会活力。
在《明末撮思》一文中,李洁非谈到晚明精神文化到达的高度,他写道,“在社会和历史质变刺激下,明末有了明确立足自我、肯定个体的个人主义私有观,以此为引导,进而有‘平权’的意识,又从‘平权’意识中发展出对君权、独夫的批判。将这思想脉络连结起来,最终它指向何方,对业已置身现代文明的我们来说,答案不言自明。”在该文“明末的高度”一节的结尾,又表示:“考虑到很多人以为中国不能自发产生民主思想和精神,甚至说至今中国人仍不适于民主,就益觉对明末历史的埋没令人痛惜。”
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洁非总结道:“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的历史转型在世界上最成功,但从中古而近古,中国的转型可谓步履维艰——从晚明到今近400年……回顾历史来龙去脉,不能不觉得从明代至今中国始终是在演述和完成同一个主题。”
■ 对话李洁非
“对历史文化了解越多
越利于我们认识病症”
新京报:晚明思想中肯定个体的、民主的因子,时至今日,仍然不大为人所知。这使我想到你研究当代文学,在时代背景与社会现象中,个人、民主、自由等因素恰好是最为欠缺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的当代文学研究和晚明思想研究相互佐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构成“病症”与“病根”的关系?
李洁非:古今结合起来质证考辨,往往使问题看得深些。比如当代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风气,喜欢唱高调,论事和做事以理论漂亮为第一,设若“政治正确”哪怕事情办砸也没关系,终于搞到“宁左勿右”的地步,大家比来比去就比豪言壮语,比谁更敢说大话和空话,以致有“浮夸风”(其实严重程度远非“浮夸”字眼所能描述)等。这股思想风气左右我们三十年,直到邓小平、胡耀邦用“实践”重订是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确系疗治当代思想沉疴一剂根本之药。它讲的是什么?是尊重事实、尊重知识、尊重科学。进一步抽取其精神,则是:重客观、轻主观。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李洁非:“大跃进”也好,“文革”也好,并非如当时执着的是什么革命啊不革命啊这样的问题,而根本是思维方式、思想态度的问题——人们说话做事,重主观冥想、轻客观考察,或者说追逐理论、排斥实践——是这样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认识。那么,为何如此?一般我们只晓得从现实找原因,有一次我读一位老先生的回忆录,他是桐城派后裔,他讲到“文革”时经历“狠斗私字一闪念”这种场面,说当时心中情不自禁地就想起幼年在家塾里面“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拈红黑豆、记“功过格”的理学那一套。可见作为过来人,老先生所见与我们不一样。我们以为“文革”是“新”的,老先生却知道那些东西本有来历,是旧物翻新。人终归逃不出历史文化的影响雕塑,对历史文化了解越多,越利于我们准确认识病症。所以等到我读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等,对当代思想风气的祖源便豁然开朗。
新京报:能否具体谈谈?
李洁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篇讲明清之际学风转变,用一句话来概括:“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给我很大启发。晚明思想很有倡扬个性的气质,但过去我只从好的或积极的一面注意它,没有想它的负作用乃至有害。明人“独抒性灵”的追求中,隐藏着“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的习气,到处是“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物,逢人作“悬揣之空谈”,争鸣义理、高标其格、夸夸其谈,后人用“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讽刺其形象,痛陈国家怎样在空谈和高调中断送。所以,经历了如此的信口开河、逞臆放言,清代学风为之一变,特别务实,特别严谨,特别注重有根有据的实学、实证。对清学这种转变,过去强调清室文化禁抑政策影响较多,实际上,吸取明代思想教训才是更内在的原因。但清末而至“五四”,受种种现实激荡,心性解放疏狂又成大势所趋,主观的情态不断抬头,客观的意愿不断下降,“革命”激情充斥每个角落,终至“大跃进”、“文革”主观精神大放纵……也正是把历史这样梳理过,我对邓小平力倡“实事求是”的中肯、深刻与高明,才有由衷体会。
新京报:这对当代的借鉴意义是?
李洁非:我觉得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使中国社会与文化长足进步,关键确实在于思想风气真正落实到“重客观”。但从现实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观放纵的积习,无论社会精英还是一般国民身上,都还相当普遍。假如有一天,各种激越调门都没有市场,大家说话做事都能具备疑义相析、讲事实重实据的素养,思想风气才可以说扭转过来。如果能够那样,中国任何事情皆有望。
李洁非语录
“今天的作家诗人不要说和陶渊明比,即便想拥有苏东坡式的从容、自由与纯粹,也是奢望。”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起码比鸦片战争早200年,也就是说,起码可以推前至晚明。”
“几十年来,不论当代文学还是其他方面的讨论、纷争,判断过剩、主观过大,安于陈述事实者少。我因为个人有所反思,而力求减少主观判断,来努力接近客观。”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